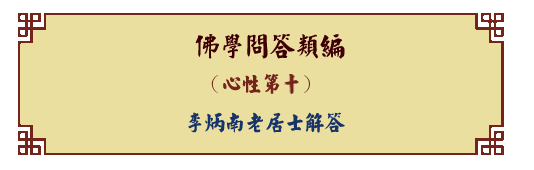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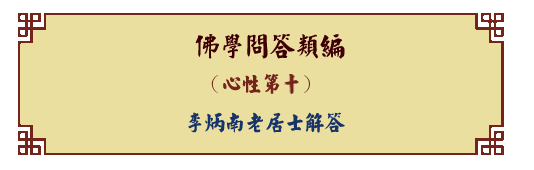
問:一切世界為心所造,心何所造?(支世榮)
答:心是真空,非可造作。
問:過去心不可得,現在心不可得,未來心不可得,意義請示!(慧香)
答:汝到「覓心不可得」時,自能了然,若我說,便去題萬里矣。
問:怎樣叫做心羅萬象?(王錫錡)
答:心如虛空(此心非指肉團心)。所有山河大地,一切一切,盡包其中。
問:人人都有佛性,佛性如何來的?為什麼會有佛性?(劉定一)
答:如此問,方可如是答,「法爾如是」。若不相契,區區亦請教一句,「空從何來」。
問:若眾生成佛時。一尊一尊列位,或總共打做一團?(潘妙玄)
答:法身惟一,報化有別。
問:回光返照及光奕奕、圓陀陀作何解釋?(戴添丁)
答:回光返照四字,世俗常用之語也。今未言明讀何書而見此,又未敘出文句,自無從解。惟見下列兩句,聯想到此句或是形容心性,只有按是解說而已。光指心光,照喻心起攀緣,凡夫之心,常向外馳,回返兩字,是把它收回來,安住本位的意思。下兩句亦當係形容性狀,謂性體本是光明圓融的意思。
問:真如與無明染熏,亦可說是眾緣和合一種的假相乎?(蕭慧心)
答:可云如是。
問:真如與無明同一身,何以真如敵不過無明,隨其輪迴呢?(李鋡榮)
答:無明與真如,無始以來,糾纏一處,各有力量。染分生染,從染入染,即迷亂不覺,常住輪迴;淨分生淨,從淨入淨,即徹悟大覺,成佛作祖。既能成佛作祖,便不宜全稱肯定,說真如敵不住無明。
問:六祖慧能大師云:「煩惱即菩提」。當如何解?(智梁)
答:佛與眾生,皆是性體,煩惱菩提,皆是性用。
問:金剛經之要義是否即在「離一切相」?(沙壬)
答:可云如是。
問:十方無量佛共同一法身,何以又分無量數名乎?(智梁)
答:法身指性,佛名詮相。
問:吾人如何境地,才可謂明心見性,學到明心見性,是證到什麼果位?(智梁)
答:見幾分,證幾分。
問:「反聞聞自性」如何解?(林夢丁)
答:耳識不向外馳,離絕聲塵,再反轉來觀照自性,以耳識之用在能聞,但以此識時起觀照,即是聞矣。
問:心不在內,不在外,不在其中,實居何處?(林夢丁)
答:說小可入芥子,說大盡包虛空,不能執著一定方所。
問:過去心、未來心、現在心皆不可得,以何心可得?念佛心可得否?(林夢丁)
答:若到念而無念,亦覓他不得。
問:世界成住壞空四中劫,成劫後住劫時,眾生出現,無明從那裡來的?(李鋡榮)
答:世界非止一個,此成住,彼壞空,錯落參差,如嘔泡之起滅。眾生神識飄蕩虛空,不定往何世界,某一個世界住時,神識投生,當係來自他方,神識本含無明,無明來自無始。
問:「情與無情」以何種因緣「同圓種智」?(金仁孚)
答:此圓教之主張,謂色與心法,正與依報,此四者無非是一佛之色心正依(色包有情無情,依只無情),並無差別,是謂「中道佛性」。若起差別,是情迷故,有一成就,餘均成就。如人身皮肉有知覺,爪髮無知覺,然皮肉爪髮總為一個人體,一個人得到官,或是得到罪,乃指一全人而言。並不能分此官罪是指皮肉,而不指爪髮,同圓種智之義,大抵如此。
問:唯心無境與觀想為空,是否同義?是否了義之說?(林火壽)
答:唯心無境,是性德之實相;觀空是修德之一端。了義兩字甚難言也,有比較之了義,有階段之了義,居士所言,乃空諦之了義。尚有假諦與中諦,如中諦之亦空亦假,非空非假,即空即假,能說非了義乎?
問:佛教講境由心變,心能轉境,又云心即是境,境即是心,心境一如,所以才說,「唯心淨土,自性彌陀」,那樣心境都是一體,譬如有人坐在棹子面前,另外再來一個人,打棹子一下,棹子不疼,打人一下,人就感覺疼,既然心境一體,為什麼人挨打就覺著疼,棹子挨打,就覺著不疼,這樣說「唯心淨土,自性彌陀」,心境一如,能講得通嗎?(施無畏)
答:此問語意何在,少欠明顯,只有分說,「心境一如」是從理說,心為真空之體,境為分別幻相,體喻空氣,相喻萬物,萬物雖多,皆不離空氣變化(含有以太),此心境之理。但萬物分有情與無情,正說有情被打知疼,無情被打不知疼,別說情與無情,既云同圓種智,便能人知疼棹亦知疼。「唯心淨土自性彌陀」,此亦是理論,明前說自解此理,若從事講,雖云「唯心淨土」,不能謂無極樂淨土,如只講心土,不能謂無歐美各國。雖云「自性彌陀」,不能謂無西方彌陀,如只講性佛,不能謂無釋迦世尊。
問:佛經既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,皆當作佛,又云即心是佛,即心作佛,那又何必修呢?不須要智慧功德莊嚴,因為當下即是的原故,然又說「三祇修福慧,百劫種相好」,豈不是多此一舉嗎?(施無畏)
答:眾生有佛性,譬如礦中有金,金被塵沙包裹,似性被無明覆蓋。金不淘汰塵沙,金雖仍是金,然不能成器,性不修斷無明,佛性雖仍佛性,然不能證佛,淘汰乃對塵沙,非淘汰其金,金顯方能成器,修斷乃對無明,非修斷本性,性見方能證佛。
問:法華經上說:「是法住法位,世間相常住」。又云「三界無安,猶如火宅」,既說常住,又說火宅,不相違否?(施無畏)
答:迷者惑亂顛倒,被業牽引受報,如在夢中現種種之像,恐怖苦惱,故曰三界火宅,覺者心明性見,照破諸妄,神通自在,無來無去,故曰常住。
問:佛性是一人一個,是一切眾生一個,若說是一個,世界人口,逐漸增加,都有佛性,那麼佛性亦會隨眾生多嗎?若說多個,每個眾生的佛性都從那裡來的?試如何解?(施無畏)
答:曾有人問,已經解答,恕不再贅。可檢閱佛學問答彙編。茲舉簡例奉答。人不忘我,亦不忘食眠,此是一種心理。試思此種心理,是一切眾生共同一個,是每人一個。更思此心理來自何處。
問:佛說萬法唯心,又說非青非紅,無形無相,又說覓心不可得,這是不是矛盾,究竟心有沒有?(沈子良)
答:此非矛盾,實則此事難以形容,故有時說有,是說本性;有時說無,恐著跡相,語皆真實。凡夫多數,泥跡迷本,若再誤會此解,則易顛倒矣。萬法唯心,是顯本性,非青非紅,是掃跡相,明乎此,有與沒有,豈得漫無分限,冒然執一。
問:洪自誠云「忙處不亂性,須閑處心神養得清,死時不動心,須生時事物看得破」,根據此四句話,有無佛學的意義?(顧賡彤)
答:有近似處,但只理論而已。閑處心如何清,生事如何看得破,豈儱侗數語,所能作得徹底耶?
問:般若心經說,色即是空,空是空無所有,何以有色?空即是色,色是有形色,何以為空?(池慧霖)
答:此問題答之屢矣。茲再為居士而說,見色說色,見空說空,是就事言,就相言。見色知空,見空知色,是就理言,就體言。茲有淺喻可以得解,夢是空,而有種種色相,是空即色也。虹是色,卻無七彩實體,是色即空也
問:觀世音菩薩以廣大神通力救苦救難,而眾生之苦難,悉為前因業力所招感之果,則於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而獲解脫時,其本應遭遇之罪報,是否即從此永遠消除可不復受報?若是則其理何在?(陳協和)
答:心能造業,心能轉業,萬法唯心,是其原理。心持觀音聖號,即染淨轉變關頭,持功若淺,則能伏業,而獲臨時解脫;持功若深,則能斷業,可得究竟解脫矣。
問:心地若然無罣礙,高山平地總西方,西方就在自己心裏嗎?(張鴻聲)
答:西方固在心裏,然非是指肉團心,不可誤會!此心盡包虛空,其大無外,豈止西方一域在自心內,豎窮橫遍,安有出乎心外者。
問:楞嚴經說心不在內,不在外,不在中間。說了一大套不對,究竟心在何處,為何不說出來?(沈子良)
答:經上說之清清楚楚,先生不能細心領會,故有此不滿。應知塵沙事理,有精有粗,解答必有多法。直說不解,便用反襯,明說不了,便用暗示,或烘雲托月,或借物印心,演者無不盡暢其旨,學者或不能盡契其機耳。世尊拈花,迦葉微笑,借物印心法也,楞嚴問心,七處不著,烘雲托月法也。
問:莊子化蝶這是怎麼一回事?(朝新班)
答:莊子思想,頗近於佛,此亦是萬法心造之意。
問:心淨即佛土淨,隨其心淨即佛土淨,如何名為心淨,其義云何?(潘妙玄)
答:粗說三毒不起是,深說念而無念是。
問:見身無實是佛身,了心如幻是本性,身與心有何殊別?(李清木)
答:身者四大假合「五官四肢」之一具肉體耳,心者妙明之靈覺,嘗言之「真如本性」是。
問:金剛經云,無法可說,是名說法,其義云何?(蕭紹馨)
答:是名說法,法指說真如般若也。此法言語道斷,故曰無法可說,其口雖不說,正是暗示真如般若密意,故仍曰說法也。
問:佛經中謂,本性乃本來清淨,那麼我們的本性,又怎會變成污穢不清,究竟因何緣故?(蕭金榮)
答:本性清淨,名曰本覺,但無始而有無明。譬如金質,便是金質,但在礦中而與沙土混合。雖則相混,但金自金,沙土自沙土也,是故金必煉而純,性必修方淨。
問:佛說:「天堂地獄唯心造」是怎麼解釋?那麼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所造的,是真的有西方嗎?以何為證?(謝碧玉)
答:解釋太費辭,今與說夢境是心造,能悟此則知彼。西方極樂世界如是假,如沒有,那便是釋迦牟尼佛打妄語,佛打妄語,居士相信乎?
問:嘗聞學佛者言經書內載眾生皆有佛性,今為證此說,請老師舉一(除人類之外者)能成初果證者可矣?(譚洪斌)
答:一切動物,總稱眾生,皆有知覺,此知覺原是性之作用。惟有悟有迷,迷時是眾生,悟時即是佛,故曰,眾生皆有佛性。鸚鵡念佛,死後塚現蓮花,天龍夜叉金翅鳥等,俱作護法,即人類外具佛性之證也。
問:佛家主張,觀法界性,一切唯心造,用心識來觀察一切,均為心識所變,這不是與巴克列的「存在即被知覺」的唯心學說相似嗎?(黃冠中)
答:巴氏之書,區區譾陋,未曾寓目。所謂「存在」究何所指,指境界乎?偶嘗閱西國學者,帛萊氏之「心觀」,霍爾脫之「論心」,皆主心外有境,今觀巴氏之「存在」,似亦說此,果如所揣,則與佛說根本不同,所謂「一切唯心造」者,遮無外境也。
問:眾生皆具佛性,這佛性是從真如涅槃中起惑而來?還是無中生有?如二者皆非又何來緣起?(黎明時)
答:佛性即是真如,無始無終,不生不滅。
問:萬法唯識,六道輪迴亦唯心造,白癡之人不知觀想,超慧哲人不信有六道輪迴,應無(不入)六道輪迴矣?(黎明時)
答:心造之造字,包括造業及現果而言。當造業時,其心雖不希求六道,但其性質與之契合,自然幻現,不以彼知不知信不信,以定標準。譬如平日三業行動,並非希求睡後作一某夢。或不信與不知某夜有夢,而屆時種子起現行,自不作主,忽現幻境,綜錯複雜,有身有物,或喜或懼;應知此境,即是心念造成,六道大夢,亦尤是耳。
問:「神通力」是否唯心所現,抑或為方便教理之比喻?(張弓)
答:萬法唯心,神通何能例外?既有其事,何能說是比喻。
問:「萬事唯心造」如遇鬼時,以此觀念起「不造」之心,可否使之消滅於無形?(張弓)
答:此甚微細,「不造」二字,諒非初機所能辦到。多生多劫,已含藏造鬼之種子,若無相當定力,種子或起現行,並非遇鬼,皆是當時念頭所造也。
問:法相以眾緣所成,故當體即空,法性乃萬有之本體,不假眾緣,何以法性亦空?(胡正臨)
答:此空即是性之本體,非空外另有物體為性也。凡有物體,皆屬於相,相必依空而幻生,此空乃無物質,非無空耳。
問:「緣生性空」,既云性空,何有六道輪迴?既云緣生性空,何者去證涅槃悟道?(胡正臨)
答:「夢裏明明有六趣,覺後空空無大千」,此答前段。本性原有自清淨,因被無明障敝,故顛倒紛紜。無明淨盡,謂之涅槃,實則法性重彰,何嘗有證有得。古人詠走馬燈句云:「若滅心中煙火盡,刀槍人馬一齊收」,可以借喻,此答後段。
問:既云本源,佛性本自寂滅,從無始來本自不動,也無生滅,此就理說,至若事(相)上之生滅來去當屬實有,如此則理事已礙,如何是理事無礙?(胡正臨)
答:佛性有不變隨緣二義,不變言其體,隨緣言其相,相有生滅,體仍寂靜。借物喻之,水係液質,納碗中則圓,納池中則方,納盤中則短,納桶中則長。液質體也,方圓長短相也,體與相何嘗有礙。
問:六祖參法性寺時遇風吹幡動,二僧爭辯,經祖開示「非風動,亦非幡動,仁者心動」,學人未明此理,若云禪宗主心不隨動故,則心雖不動,但風幡自是動何,是否心能轉物,以令風幡俱不動?(胡正臨)
答:風與幡皆是相,應知萬法唯識,非別有風幡及外境!凡夫迷境不了真心,智者明心知無妄境,所謂「夢裏明明有六趣,覺後空空無大千」也。明乎風幡乃識田種子現行,則不誤會心自心,風幡自風幡矣。
問:真如心性乃天地靈氣所賦我之真我?死後是否仍歸天地?若如此求證涅槃,念佛求生者究竟是誰?若不歸還是否占為己有,其理為何?(胡正臨)
答:天地二字,得非指頭上之藍色氣,足下之黃色土乎?此範圍太小矣。佛家只言心造萬法,無量大千世界,亦為心造,未聞天地能賦真如。俗云之靈魂,佛家稱曰識神,是為心起無明而變,此身死後,識神被業牽引,輪迴六道,生死不息!並非散滅,何有歸還天地。若說己有,亦可方便云云,然當知浩浩空氣,城中有,野外有,瓊樓綺閣中有,雞栖豚柵中有,大缸中有,小盞中有,請問此氣是上六者之己有歟?非己有歟。
問:上承賜答中「心造萬法……心起無明為識,識被業牽輪迴六道……」,如此則吾人之心又從何來?(胡正臨)
答:「法爾如此」,無所始亦無所來,無所終亦無所去。初學驟聞此答,似屬儱侗,必深研若干年,方能明此為究竟之語也。吾人之心,如是!如是!
問:此一真法界諸聖所見無自無他,清淨本然,凡夫所見自他分明萬相森羅,處今原子電能時代,物質異昔昌明,用以戰爭殺傷何止千萬,如此說來,心物似乎對立,如何是三界所有唯是一「心」?(胡正臨)
答:原子電能,亦是心中事,戰爭殺人,亦由心中發。
問:既是「見與見緣,元是菩提妙淨明體」,心物之是一如,何以「迷已為物,被物所轉」即將「輪迴是中自取流轉」,是義難明尚望示明?(胡正臨)
答:此條但畫「」號,未舉出自何典,無法檢討。且有數字繕寫不清,並不便率爾奉答。
問:眾生皆有佛性,佛性本來是清淨光明,萬德萬能。那麼凡夫本來是佛嗎?佛是覺悟者,為何起一念無明,受了生死輪迴苦,自己不能解脫呢?凡夫修道能成佛是有道理,可是本來清淨的佛性起無明轉變凡夫,很奇怪!(呂正涼)
答:佛性與圓滿法身佛,是一是二,解有分限。佛性有「本覺」「不覺」「始覺」「隨分覺」「究竟覺」之不同,然皆混稱曰佛性。圓滿法身,則專指究竟覺性而言。譬如金在礦中,泥沙揉雜時,採淘時,熔冶時,提煉時,鑄成器皿時,皆可混稱曰金,此即佛性之總喻。居士未明斯義,故有「佛是覺悟者,為何起一念無明」之誤會。再知金在礦中,原雜泥沙,雖云是金,尚是礦石。佛性未覺,本有無明,雖具本覺,自是凡夫。
問:「三千大千世界」是指凡夫心否?(許玉霞)
答:說是心所現,比較明顯。直稱為心未嘗不可,莫如體用分講,初機易悟耳。
問:人之壽命,依於命根,命根又依於心,然則心欲求長壽,亦可得長壽乎?(鍾鈞梁)
答:妄心是生滅法,可求長壽。真心本無生滅,長壽又何所加乎?
問:在某一書裏有說,有一位老婆婆問一位大德說「金剛經裡不是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心不可得,你要用何心來得這個?」這位大德聽了莫能答,愴惶離去。請問您老人家為後學解釋,要用何言去答覆此老婆婆說的話?(林良柱)
答:此宗門機鋒語,乃當機指心之要法,不許後人如訓詁講章,向人盲道。居士既非賣餅婆婆,區區亦不吃汝點心,何必纏這葛藤。
問:常聽老師說,佛的法身是盡虛空遍法界,法身佛能來救度眾生否?(阿鸞)
答:法身既遍虛空,何有來去,惟法身無相,所度之眾,皆是上根上智者,中下者則不知不悟耳。
問:煩惱即菩提,生死即涅槃,是作何解?(周慧德)
答:「即」作就是之義講解。性合妄即名煩惱;合覺即名菩提。妄時虛假,有生有滅,故曰生死;覺時歸真,不生不滅,故曰涅槃;雖似二其實一也。煩惱菩提,乃合妄合覺之理,生死涅槃,乃生滅不生滅之事。猶水之與浪不過動靜有別,明乎此喻,思過半矣。
問:成佛的情識,與凡夫死了後的情識,是怎麼樣的分別呢?(田倩君)
答:佛性清淨光明,如大圓鏡,名曰究竟覺性;凡夫心性煩惑重重,如珠裡灰塵,一團黑漆,名曰「情識」。生前亦如是,死後亦如是,此其分別也。
問:佛學中所說的「無記性」,與告子所主「性無善無不善」,是不是有相同的意思?(田倩君)
答:告子所主,是指動物之性體而言,佛學「無記」,是指初次動作之因性,此其不同處。
問:諸法皆有佛性,那麼所謂天體、植物、礦物、液體、氣體、固體也各佛性嗎?甚麼原理?(葉慶春)
答:區區尚未聞有此說,恕不能答。
問:「明心」須要心悟,而心悟的方法如何?怎樣叫做心悟?當心悟時,自身的靈魂與肉體,竟有何種感覺?才可叫做心悟?怎樣叫做「見性」,見性時的肉體和靈魂等感覺究竟有如何情況?(謝元甫)
答:性本靈明,因被身、邊、見取、戒取、邪等五見惑;及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等五思惑,遮蓋得昏昏迷迷,此性被迷,變作靈魂,以故業引投胎。「悟」者悟此本性原來清淨,悟上十事,皆是本性障礙。「明見」者能斷以上十事,本性顯露也。其修法或禪或淨,自必下一番功夫方得,此非肉體之事,然功夫漸進肉體亦起一種感動耳。再進一言,若欲起修,誤投外道,禍且不測矣,亦須慎之!
問:已故的法舫法師生前曾著「有的研究」一文,大聲疾呼的糾正一般僧俗佛徒中了空毒。所以舫師提倡「有之研究」,實深合我心,可是今日佛學園地,仍是空毒遍佈,奈何奈何?(堯澤)
答:舫師糾正何種之空,提倡何種之有,佛學園地,何種議論是空毒,均未見示,不敢率答。應知空有問題,乃佛家主要學說。發揮至精至盡,蓋真空妙有,非二非一,在體相事理上可分別言說之,在實際上卻不能打成兩橛。心經之「色空不異,色空即是」四句。楞伽之「五法三自性」,圓成實性等,訓語皆明,若能下一番功夫,自不至執空執有。所宜呵斥者,謬解佛法之世俗妄有頑空而已。
問:煩惱不斷,亦可名曰生死不斷是否?(蕭慧心)
答:名不必如說是,總是一事一名,比較清楚易懂。論理煩惱未斷,則生死不了,乃是一說因一說果耳。
問:不執空,不執有,要作中觀,是指世法與出世法兩道合觀,為圓融無礙,隨順眾生成就方便之法否?(蕭慧心)
答:空與有,不能強分作世與出世,乃是包括一切諸法而言,即物說有,離物說空,皆是執著偏見;能解澈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,方是圓融無礙之中道。
問:般若波羅密多心經,雖經斌宗法師解釋心之一字甚詳,譬喻雖多,鄙仍不明真心之究在人身何處?祈示知俾明下懷!(吳亮輝)
答:這話說來頗不易懂,縱說之極詳明,尚須有一番參悟,方能瞭解。此心原係空空無體,若以物質求之,則謬之千里。知是,則心念所至之處,便是心所在處。經云:不在內,不在外,不在中間等,其言至精,試思各人之心念,有定所乎?如疑此語儱統,且看儒家之語曰:「放之則彌六合,卷之則退藏於密」。請參密在人身何處!
問: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八分云:「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」,此四句偈是指「無我相,人相,眾生相,壽者相」否?(翟孟秋)
答:此問題古今諍論甚多,最圓融之說法,即是擇經中任何四句,皆得謂之四句偈,不一定泥指四相及六如等,而即便指四相及六如等,亦未嘗不可也。
問:金經第三十分云「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」,「事」字指六根、六塵、妄念?(翟孟秋)
答:指一合相句而言。
問:金經三十分云「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」,是指眾生之妄念之多,或是另有所指?(翟孟秋)
答:即本句解本句,暫不宜牽扯上下之文,因上下之文,自有其講法,此只說大千碎為微塵,即照本句講便妥,何必節外生枝。
問:金剛經分第十應無所住而生其心,及分第二十六「若以色見我,以音聲求我,是人行邪道,不能見如來」如何解?(王錫錡)
答:無住是不取著,生心是生清淨心,其義即不著一切相,而行六度萬行也。下偈「如來」指無相之真如法身,前兩句謂俗人但以三十二相求見如來,第三句謂如此乃偏錯用心也。初學宜先讀八大人覺經、四十二章經、十善業道經等,若求名相,可讀梅擷芸居士之「相宗綱要」,以期認識門徑。若開首即閱般若,猶才入幼稚園,教以代數幾何之算法,授以左國班馬之文章也,其不惑者幾希?
問:自學佛以來常聽經聞法,始知此心,在聖不增,在凡不減,無形無相。若言其有,視而不見,若言其無,靈靈覺覺。整日亂跑亂走不肯與我相見。後聽般若心經之時,有徹見心,具足三智之語,但是三智之理,未得徹底。請師再詳細解說。(慧德)
答:能明一切法之空相,謂之一切智,聲聞緣覺所證也;知一切種種差別之道法,既照其空,又了其假,謂之道種智,菩薩所證也;照空如聲緣所見,照假如菩薩所見,融會通達,皆見實相,謂之一切種智,佛陀所證也
問:既諸法無常,一切都由因緣和合連續而起,幻起幻滅,絕無實在,何以復有涅槃真如之說,若能達到真如,則無常之外,應仍有真實永恒之存在?(徐公起)
答:諸法之相有二,一者色相,一者空相。色相為緣合而假有,空相原如如而真空,假有色相,依於緣起,自屬無常。真空空相,本於性空,故無生滅。然空即是色,色即是空,不可偏執,若解中諦觀,自不致疑團橫胸矣。
問:「非有非空」,是指一切生滅之相,法身是否亦「非有非空」?(胡之真)
答:法身正如是耳。
問:吾之靈魂從何處來?(陳榮進)
答:真如本性,一念不覺,而有無明,性既無明,則稱為妄識,此種妄識,凡夫即尊之為靈魂。
問:大乘起信論中,「心真如者,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」作何解?(沙壬)
答:此只可略解,若求其詳,須參各家註疏。先釋首句,心指本性,真如是真真實實,不變恆常之義,獨心如是,故有此稱。次釋二句,一切事理,統名曰法。然一事有一事之界線,一理有一理之界線,故曰法界,將所有之一切法界合觀,曰大總相。出處曰門,依處曰體,法所出處依處,故曰法門體。再合講之,即謂此心為何,乃是一真法界整個總相,由之所出之門,依之而起之體也。
問:覺者之本性及有情之神識起初從何處來,從何物產生乎?(智恆)
答:此問題本言無始,若言何處何物,即為言始矣。言始者理不圓通,外道好言始。反問一句,彼所言之始,又從何來。
問: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菩薩,及一切有情之共計數量,在無始比現在有無增減?(智恒)
答:體無增減,相有變化。
問:有情與無情之別,是不是有靈性與無靈性之謂,若此據聞南洋有一種「食人樹」,凡觸鳥獸捲抱至死,是不是有靈性之表現?(林柳淋)
答:情指貪瞋愛惡之情識而言,「食人樹」乃係一種遇觸起變化之植物。如此方含羞草,以物觸之即閉,其理相同,不過樹與草力量大小不同,草木非有情識耳。
問:動物皆有靈性之謂,如大象之動物,亦一個的靈性,如微生物之細體,亦一靈性,究竟靈性之大小如何?(廖武卿)
答:性本豎窮三際,橫遍十方,無有大小。若論靈頑,則有假相區別,各個不同,然亦不限軀殼大小而定其靈之大小。試舉大象與小猴為例,猴軀雖小,而性之靈敏,實超過象之多多。
問:「自性」涵義如何?自性法身,自性親因,自性煩惱,自性眾生等等之「自性」,是否相同?(周邦道)
答:自性即真如本性,清淨本覺,無始而染無明,轉為業識,而自性依然無損,此名眾生心,即是自性眾生。其淨分之本覺,即自性法身。轉識後具有染淨二分,能互相薰,即是自性親因,其染分即是自性煩惱。
問:清淨真心、性、真如,是一是二抑是三?(大寬)
答:是一而異名。如頭、首、腦袋、腦殼之繁稱也。
問:緣起性空與性空緣起,其意義是否相同?並願略為解釋。(呂順運)
答:萬法空無自體,其相其用,均由多緣集起,故曰緣起性空。此二句意義小異,一從因說,一從果說。佛經中此例甚多,如「隨緣不變,不變隨緣」,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之類,釋者皆有二種講說,故曰小異。
問:佛學關於人之初的性,如何解釋?(呂正涼)
答:佛學言性,以天臺教義而論,本具染淨二分,薰淨則善,薰染則惡,而且只言無始,不言其初,以其初之前尚有其初之其初,故曰無始本覺(淨),無始無明(染)。因無始有無明,故入胎出胎,流轉至今,是無始以來,已有多次眾生假身生生死死,非止現在始有身性,故「初」之一字,實莫能定其位耳。
問:「人之初性本善」中之「初」,所指者為原始之初,或者出生之初?(呂正涼)
答:此儒家一派之說也,儒家只講世間法。人初性善範圍,當指出生之際。
問:關於儒家所講的性,與佛教所講的性,及科學者所講之性,其善惡關係不甚明白,請略述之。(呂正涼)
答:儒家言性,其說不一,孔子說性相近也,習相遠也,孟子主性善,荀子主性惡,楊子主性善惡相混。佛家稱性體曰真如,各宗主張亦有小異,法相宗主張此真如是三性中之圓成實性,為一切有為法所依之體。三論宗主張為真空(妙有即真空)。華嚴宗主張有不變隨緣二義,如水遇風興波是隨緣義,波與水未改溼性是不變義,即是說體上無染淨,而變後有染淨。天臺宗主張本具有染淨二分,此不過粗述大略。科學家偏重物質,對心性不甚研討,未見有言性專書,不能舉答。
問:科學者說的「先天性遺傳性格」、出生當初皆「有善有惡」,這個學說和「有善無惡」的學說不一樣,這兩說都是偏見嗎?(呂正涼)
答:先天遺傳,有善有惡,與有善無惡兩說,皆指起於作胎,終於出生之一段,自各有其理。然皆似是認為先有胎質,而後有性,並不能窮性來源,及性秉夙習,理未周圓,可說是偏。
問:無始之時,豈不都是善人。何故起造惡業或無始就有惡人?(慧祝)
答:既曰無始,何能定時,若但說人類,可從世界成時論起。按小乘經,斯時一切自然,無有競爭,可云是善,惟所秉之性,而有無始無明,遇緣就會造作惡業。
問:釋尊答富樓那問「覺性清淨本然,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」。云「性覺必明,妄為明覺,覺非所明,因明立所,所既妄立,生汝妄能。」竊以為在覺性清淨本然之時,十方虛空同一清淨性海,既無中邊,復無客塵,猶如光天化日之下,無一物成蔭,當無明暗分別。又譬如一室萬燈,各各等明,燈燈相照,當無能所可立,不知此一「妄為明覺」之「妄」因何緣而生?尚乞明示以啟愚昧。(蔣南海)
答:覺矣自明,明覺非二,此真諦也。不解此理,欲與覺上另外加明,此即迷妄作用。富樓那尊者,彼時根本無明未盡,故有此妄解,是其因緣也。
問:經云「業力甚大心力更大。」前時無知造作惡業,後即懺悔,臨終忽發大善念便不墮惡道者,是心力大於所造業力乎?又雖臨終生懺悔心,起善念尚墮惡道者,是業力勝於心力乎?(許炎墩)
答:如是如是。
問:佛嘗謂阿難云:「人有今世為善,死墮地獄者。今世為惡,死生天堂者。阿難問何故。佛言今世為善,死墮地獄者,今世之善未熟,前世之惡已熟也。今世為惡 ,死生天堂者,今世之惡未熟,前世之善已熟也。熟處先受報,譬如欠債急處先還。」如是者隨業力所轉,無心力之作用乎?(許炎墩)
答:世尊此段所說,係答阿難此問,此外尚有多義,俱載經論,何得斷章取義,遽謂心力無用。要知業由心造,業由心轉,但須看心造業力與轉業心力何者強弱而定。今設一喻,風寒吹水成冰,風暖吹冰還水。若數尺堅冰,暖風在嚴冬之時,僅吹半時,冰必不解。此風暖力不勝冰寒力故。陽春之時,暖風連日不息,冰不半時而化水,此冰寒力不勝風暖力故。
問:在無始以前,真如不守自性,忽動妄念,致起無明,由此而有眾生,而有生滅。此真如奚自而來,何忽然不守自性?以何因緣,而至於此?又此真如與諸佛菩薩及三界眾生人人本具之真如是一是異。如其是一,何以有覺有迷。如其是異,則此無量數之真如本體,最初何自而來?(張劍芬)
答:是須分段作復。一、「此真如奚自而來,為何忽然不守自性。」此真如亦名如來藏,從無始來,(不可曰無始以前,緣稱無始,何有始前。)本具有染淨二分,染指無始無明,淨指本覺。如金在礦,雖具光明之質但與塵沙混合,不能顯出 。修行人順本覺生起覺悟之知,名曰始覺。如金礦之質,經過熔煉,汰去塵沙,然煉後之金,與在礦之金,實非二物。佛家言無始,為最圓澈之學說。如必求原始,試問一直追上去,有窮盡乎。二、「佛生真如,是一是異。」此可借物作喻,日光下空氣暖,冰窖內空氣冷,佛殿上空氣香,廁所間空氣臭,藥店中空氣苦,糖廠裡空氣甜,靜思這些地方之空氣是一是異,可以了然。
問:「假使百千劫,所作業不亡,因緣會遇時,果報還自受。」、「罪性本空由心造,心若滅時罪亦亡。」讀上二偈頓起疑念。百千劫之業都不亡,何以說罪性本空 ?心滅與忘罪有何不同?必怎樣滅?如念佛豈不是忘罪,何能滅罪?如懺悔能滅罪,無明火起時,殺人造罪,過後生大懊悔,能滅罪嗎?帶業往生假使經百千劫,業又不亡怎樣辦?(白痴)
答:此一條問,有不同之意四,須分答之。初段罪業不亡,是說種子,種子者,如電影機內膠片,其上印有凶惡之跡象。心造之心,是說本性轉成之妄心,本性如膠片之本來面目,元無一物,妄心如膠片已有染痕。遇時受報,是說為環境支配,發生苦受,此如電力鏡頭機件,種種配合,銀幕上即現可怖之悲劇。然真性空無形體,不生不造,其生而造者,乃無明之妄心,但妄心依於真性,如膠片之跡象,依於膠片,假使無明滅,而真性顯,真既顯矣,而無明尚無所立,何有業種存在,業因不存,安結罪果。如膠片本質顯露,印象已滅,銀幕上亦無劇情矣,此心滅罪亡之理。復次念佛之功,淺能伏惑,深能斷惑,惑無緣不起現行,伏斷均能使果不結,此念佛滅罪之理。復次,生大懊悔,乃悔其已往,後不再作之義,此不過由惡轉善之初步,必從此真實,外不造三惡業,內斷滅三毒因,此是名真懺侮,準上段之理,罪可消耳。復次,帶業往生,非說帶業成佛,極樂五塵說法維何。無非勸修啟悟,為斷惑業,有人天聲緣菩薩之別維何。是明隨分斷惑,隨分進果,曉此理則無此疑問矣。
問:在觀無量壽經上品上生章上說到,如有行者能發三種心,即得往生。「生彼國已,見佛色身,眾相具足,見諸菩薩,色相具足,光明寶林,演說妙法。聞已,即悟無生法忍,經須臾間,歷事諸佛,遍十方界,於諸佛前,一一受記,還至本國。」其中意謂行者在很短時間內,隨阿彌陀佛,到十方諸佛前一一受記,我們知道世界無量無邊,諸佛無量無邊,無能以一有限之量(行者一人)到無限量(諸佛)前一一受記呢 ?在數理方面來說,即使在很長很長的時間,亦無法遍十方界,在諸佛前一一受記,何況在須臾之間呢?這是不是一切唯心造的觀念呢?(張葆衡)
答:眾生之身,分胎卵溼化四種,前三種在水陸空之行程,自必按其所行速度,計算里程。化形身又分有質及無質之別,無質者以神識為體,此神識之行動,以思想起作用,便不受質與路程限度,豎則一念萬年,橫則一念遍虛空界。極樂之身,便是神識所化,遲速遠近,皆隨其意。茲舉一喻,光線傳達最速,星光射在地球,必須幾百萬年所謂光年,但人看星,一念之頃,遍空之星,盡覩之矣,明乎此理,則不疑也。
問:地藏菩薩本願經講話第十七章第一節所謂「般若如大火聚,四面俱不可觸,觸之即焦頭爛額,喪身失命。」禪德說「此法如金剛王寶劍,魔來魔斬,佛來佛斬,魔佛來魔佛俱斬。」不但魔斬,連佛都要斬了,在這種離四句,絕百非,絕對絕待的境上,連佛說都不可說……等不解,懇求指示。(張啟明)
答:此是解粘去缚,離相指心之大權巧語,非大祖師不能說,非遇其人不如是說,居士必求了此法語,先向真如實相,無相無性處,下一番功夫,自能領會,否則,今日語不契機,反成鴆毒矣。
問:無記性,捨受,請舉例以明之。(嵩石)
答:於現世來世存心自他兩利之動作,其性質屬於善,反此者屬於惡,若存心動作,與上二性皆違,不能記別其固為善為惡,亦不能定其果報得苦得樂,此種性質,名曰無記。甚難舉例,茲勉說一事,不過略得彷彿,今有一人,無意中提筆在几案上寫了一個「休」字,不一時來了甲乙丙三個人,甲想休妻,正不會寫這休字,看到几案上字,回家便「休」了妻子。乙正想寫信勸人休訟,也是不會寫這「休」字,看到几案上字,回家便給人家和解了訟事。丙毫無所為,看到几案上字,並無若何感想,就過去了。然在寫休字之人,原是空空洞洞,其發生的結果,竟有善有惡,有不善不惡,而無意中提筆寫字之動作,其性質可以說無記。心身離開憂喜苦樂之領受,而得到之中庸境界,名曰捨受。此無法舉例,因人之心理不同,若強舉例,反引爭論也。
問:學人思想雖傾向理論之相宗,及實行之淨宗,但對於談空之金剛經、心經等般若經典,亦甚喜歡。如金剛經云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既云「生其心」,當非頑空。可是古今大德之一部份言論,學人常感覺每有違反佛意墮入頑空之嫌。如古德云「佛說一切法,為除一切心。」如果「除一切心」,那麼掃除了菩提心、掃除了慈悲心,不是糟糕了嗎?常見一部份僧俗佛徒,心腸鐵硬,見苦不救,是否中了「除一切心」之毒。那麼所謂「佛說一切法,為除一切心。」是否亦有頑空之嫌?是否亦係「損減執」?(堯澤)
答:「為除一切心」之心字,指妄念說。念皆是識上之分別,如第六識之分別此易體會者,至七識緣八識之見分,則甚微細,不易知矣。必到一切緣影皆無,真心方顯,故曰須一切皆除。此亦宗門究心功夫。至云菩提慈悲等,實乃性中本具之德,障不破多隱而不現,實無法除去,故除者非指此等。彼見苦不救者,正是性德未現之過,並非已將菩提慈悲等除去也。又我輩凡夫慈悲名眾生緣。菩薩慈悲名法緣,皆著迹相。佛之慈悲,本無所緣,是謂無緣大慈大悲。眾生及法二緣有相,尚可除其相,無緣則無除可除矣。頑空乃不解空色相即之理,而偏於半面者,與此不同。
問:(原函過長特節錄)金剛經大乘正宗分,這一分是佛答善現所問「應云何降伏其心」的肯綮方法。試問度眾生與降服自己的妄心,有什麼相干。六祖說見性成佛,先要認識自心眾生……認識這一點,就知度生是自度,不是度他及度牠,煩惱是無始生死根本,必須把這一類的妄心,連根拔淨才能見性成佛。有一眾生未度,是尚留一個生死種子,未拔完。如是解說與上文「應如是降伏其心」文義相符。佛度徒弟雖多,也只以人類為限,不說世界人類未度完,就是印度他的徒弟也沒外道多。此數語是對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起疑。(牛慶譽)
答:金剛經註釋繁多,各有精義,居士所解,只是其中一說耳。若僅度自心眾生不度九類,亦與本分所有一切眾生之類以下諸文不合。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之句,此是宏願,且是假設之辭,看下文「如是」二字自明。
金剛般若,是大乘教法,以平等度生,決不僅限自心或其一類。如謂度生與降伏妄心甚麼相干。古德曾有說明,小乘智力未充,耽樂涅槃,恐起度生,不能安住背念,故說降伏妄心之法,使如所教住,而驅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,即是上求下化之心,此一句最為重要,在第二分中「汝今諦聽至如是降伏其心」已指明住以此住,伏以此伏。大般若經曰「善現白佛,求無上菩提,應云何住。告曰當於一切有情住平等心(中略)及修六度等,亦應勸他 、稱揚他、喜讚他,為之自他兩利」。發菩提心論略謂「不捨有為,不住涅槃,為度無邊眾生,是深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各經論中可引作證者甚多,不能枚舉,若截去此句,只講「何住何伏」,當然不能聯貫,再若僅限自心,不為九類,似落自了漢矣,恐非本經之旨,敝見如是,尚希另質高明。
問:臺北敝友某君的去信耶穌,據說不是他要信耶穌,而是耶穌的靈要找到他。竊思某君曾經看了不少佛書,竟致「耶穌的靈找到他」,或許也是中了空毒,以致心空無主,而被耶穌的靈勾去。未知長者看法如何?(堯澤)
答:某君恐是讀的死書,雖多何為。故紙縱鑽百年,還是癡蠅出不去窗子,中空毒尚是進步中的錯路,此尚談不到。真中空毒之人,大概是一切不受,又豈肯接受什麼靈。
問:百法二十四不相應中,列有相應一行,依起信論解釋心王心所,知相與緣相同的名相應行,不同的名不相應行,何以又把相應列在不相應中?請求開示。(牛慶譽)
答:「心不相應行」乃百法五種之第四種,此是一綱,言此二十四法,異於心所有諸法與心相應也。此中「相應」乃是第四種綱之一目,所言之相應,僅指因果事業之和合相應,非如心所有之與心相應也。
問:圓覺經卷上,清淨慧菩薩問章,佛對清淨慧菩薩言「善男子,圓覺自性,非性性有,循諸性起,無取無證」、「非性性有」這一句是何意思?「循諸性起」中的「性」字是指什麼「性」呢?(陳炳林)
答:所問之兩句,乃從前問而來,知其問,方能解其答。前為清淨慧菩薩問,圓滿覺性,云何佛菩薩眾生,各有差別,故答「非性性有」,「循諸性起」等句。非性者,謂十界之差別不同,非性本體。性有者,謂隨緣而現有十界差別。諸性之性字,指隨緣起後之「性有」即種種之差別也。
問:我時常這樣想,人生自性何期得清淨,何期自性得不生不滅,何期自性得具足,何期自性得無動搖,何期自性得萬法。(胡美月)
答:此須分「理」與「事」二方面答之。先以理說,性之本體,本自清淨,不生不滅,一切具足,無有動搖,萬法皆備,非從外來,非待何時而備,無過現未來方有,人人皆如是,人人皆不知耳。再以事說之,因有無始無明,而起諸惑,遂妄攀緣,妄造諸業,妄受諸苦,以是種種,便成障礙,而本有功德,如蓋、如結、如纏、如縛、不自在矣。倘肯放下諸妄,真性自顯,何時放下,何時即顯,說到放下,諒非貴居士所能辦到,只有借諸佛力,將心送到西方,把持住阿彌陀佛,那邊把持得緊時,即是諸妄放下時。
問:人生之思想因何前念後滅呢?(胡美月)
答:此等問題,非是初學所能明瞭,即為解說,亦恐難悟。在教相未明時,雖有才智,亦不能越級而超,勢所限也。茲為略述,生則有滅,不生則無滅,此其原理。心念若生,自然有滅,若使不滅,只有不生,而真性確實不生,故亦不滅,念生於妄,故亦有滅,若進一步,悟入不二法門,生與不生,又皆平等。(附)有佛法導論,及初機淨業指南等,兩種小冊,可先看之,能依之起行,而得受用。玄微之理,須待機緣成熟,方能悟入。
問:「當知虛空生汝心內,猶如片雲點太清裡。」是說真心?是說妄心?請解為感。(林寬修)
答:真心與妄心,原非有二,不過迷覺之別,即迷時為妄,覺時為真。如海靜時為水真也,動時為浪妄也,水與浪非二,亦只是動與靜之不同耳。
問:人人之佛性本來清淨,何以會起無明?成佛之後,也是返復清淨之佛性,那時是否會再起無明?(林慶勳)
答:此非初學能解,即與講說,恐亦不能頓悟。茲舉古德之喻,希略體會而已。金必在礦,礦乃塵沙,金自光明,沙自穢垢,是有金即有沙也,佛性無明,亦復如是。金經陶冶,不再挾沙,性斷無明,不會再迷。
問:茲者樹刊問答有云「萬法皆性」,又云「無明非性乃障性之事」斯義殊不能達,蓋無明亦法也。既曰萬法皆性,則無明亦性矣。何故又言無明非性,乃障性之事。能障所障,自是非一,如礦土障金粒,礦自礦,金自金,斷不能謂礦土即金粒,推知無明障性,性與無明乃為二事,如是則萬法皆性一語,云何成立?(李蓮階)
答:性覺則明,不覺則無明,明是其本,無明是妄。妄則幻境,境即萬法,萬法既幻,皆無自體,是性隨緣之用,非性不變之體。如目有病,則生空花,花依於病,病依於目,是病依附於目,非目本體是病也。病障目明,無明障性明,喻不取一,隨機而設。又幻妄起時 ,言有能所,幻妄滅盡,能所皆無。又云性與無明,乃為二事,非不成理,但是偏執,不聞水之與波,非一亦非二乎。
問:真心是一是眾?(劉慶明)
答:此問題,非初學所知,方便說之,恐先入為主。真實言之,反引種種之疑。有問不能不答。參悟仍須多聞。真性之體,是一非二,真性隨緣,似眾不一。所言是一似一,意自不同。
問:心的本體在空間上說是橫遍十方,那我的心如此,你的心如此,眾生心亦如此,結果要擠到那裡去呢?(劉慶明)
答:一室一燈,光滿全室,若裝千燈,燈燈有光。一燈之光,已滿全室,九百燈光,擠往何處。
問:禪宗有「明心見性」之法門,吾們如何「明心」及「見性」後之心境如何?(張進添)
答:性是本性,心是真心,心性二字,在禪宗多不分講,即有時說心,有時說性,然實指一事也。在相宗則心性每分言之,雖分言之,不過動與不動之間,仍非二事,區區亦是粗略解釋,此乃佛學根本問題,初學者實不易聆悟。心性本自空明,後迷而染,則顛倒妄思妄見,即生死六道而無了期,佛有多法,遵之而修,可斷見思妄惑,斷後心性即明即見矣。明見謂之覺,此覺有深淺大小,不能一概而論。
問:所謂悟道(悟無生法忍)與明心見性其義同否?(王居士)
答:此應參考第一答,不可誤一悟即是皆悟。悟道之本,即悟無生,如與心性強分,心性言體,無生言相耳。
問:有人問:真如本性為何無始有染一念無明,即變神識輪迴投胎,但是無始未染無明以前是怎樣?(童瑞珠)
答:此須先明文理。「以前」二字,乃對某事開「始」而立,既有開「始」,纔能說開「始」,「以前」,若無開「始」,何有「以前」。佛家言性言無明,都曰「無始」,彼人偏要問「以前」,是對「無始」之義,未加研究也。
問:他又問心有幾種,究竟真心在何處?(賴阿里)
答:有三、有八、有多,各有其名,非無學者可解,故亦不為列舉。若問真心,千聖不傳,問在何處,請他破上千年功夫,自己覓去。
問:體若空,相由何而生?(陳泰樹)
答:解此問題,須先將體與相之定義說明,即不致誤會矣。體指本性本質,相指一時所現之形,相則各與假名,體則並無其實,經曰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,故說真性空,假相有也。茲舉事以證之,如一銅缾,其缾是名相也,其銅非即是鉼,此鉼為銅片之合相,去銅片則無鉼。細思之,鉼只是鉼相,而鉼並無本有之鉼體,故曰體空,體空者,相之體非相本體也,不過因他緣合,而現此相耳。銅片亦名也,乃銅屑合成,依前例推之,至於無始,總無某相本體。
問:「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。」可見無體即無相。(陳泰樹)
答:有相是說其事也,為之假有,無相是說其理也,為之真空。體既推究歸空,現相自是緣合假有,謂為假有,故亦說是無相,無相者乃三空之一也。淺言易解曰假有,深言難解曰真空。
問:陽明稱心無無念時,天機不息,一息便死,六祖亦有一念絕即死之語,請問人死後之識神,是否無念?又人死為鬼,鬼亦有念否?(鍾鈞梁)
答:如如不動,是謂真相,一念纔起,全真成妄,此是性德,背覺合塵。放下萬緣,一念不起,寂寂惺惺,全妄還真,此是修德,背塵合覺。背覺者轉智為識,背塵者轉識成智,識神是妄,所以起妄念,妄念不停,所以入六道。
問:本性好比海水,神識好比波浪,因之本性與神識是一件事,不過性一起妄念則變為神識,妄念去掉則復為本性,然否?(鮮純賢)
答:大致如是。
問:眾生入胎降生後,本性是否隨著報身來去,或隨著神識在六道輪迴中轉,抑或本性仍與整個不分的本性成為一體?(鮮純賢)
答:此問與前問何又逕庭。以名相不清,故有誤解,茲與略釋名相,問題可自解決。一眾生者,五陰四大,十二因緣等,眾多之法集合,而成此生命,此必神識入胎以後而共備,非具備以後而入胎也。二降生者,乃有證有得之聖賢,倒識入胎,出現救眾者之稱,猶從高就下,故曰降生,我等凡夫,隨業受身,只可曰出生也。三性與神識,前件既云性識一事,今何又有性隨報身,或隨神識之疑。性迷則變成識,識覺則復其性,復性則如如不動,無有輪轉,成識則分別造作,而有六趣。四本性整個,本性無別,皆真如故,神識多端,染變各異故。
問:眾生皆有佛性,而且佛性皆是盡虛空遍法界,若有多數眾生,發大心破除了我執以後,則各眾生的佛性是否合而為一或仍分屬各眾生?(鮮純賢)
答:空氣包全球,全球一空氣,十方三世佛,共同一法身。其餘疑者,參第二答。
問:實相念佛是禪是淨?抑亦禪亦淨?(鍾鈞梁)
答:一切行持法門,屬於修德,真如無為,屬於性德,修德是權,皆方便也。性德惟實乃歸元也,所謂歸元無二路,方便有多門,萬法無不如是,不獨禪與淨也。禪淨乃名相,皆是方便,心性真實,方是歸元,實相者無相,即真如法身等之別名,實相念佛,心佛一事也,到此境界,何有禪淨。
問:在家必讀內典「佛說七女經」第七頁第二行「我欲得無根、無枝、無葉之樹,無形之處,無陰陽之端,深山大呼,音響四聞,不知所在」。請問老居士此之指何處?希望詳加解釋?(李榮棠)
答:此皆係真如法身之事,安有其處,言語道斷,心行處滅,二乘不知,佛不能說,在於參修自證,非是千聖能傳。區區何人,而能詳加解釋。
問:「本性原清淨光明」蓋清淨即光明,染汙即黑暗,近閱菩提樹一二三期三三頁天臺宗簡述。謂自性本具善惡等法……他宗雖言性具善,不言性具惡,此宗獨言性具惡,又言善有性善修善,惡有性惡修惡,眾生成佛,但斷修惡,不斷性惡,此與佛說,豈不大相逕庭耶?(賴棟樑)
答:天臺教義一出,率多宗之,但性具善惡,學者依違紛然,旗鼓相當,未見勝負,倘必討箇分明,恐證等覺始知。若說與佛逕庭,便是否認其說,蓋三藏浩浩,銓釋不同,天臺如無別解,豈肯自違聖言量耶。
問:本性不可分,為一整體,但眾生尚未明心見性,以前的本性是否能與佛的性合為一體,或不能稱為本性?(鮮純貧)
答:佛與眾生,性皆可稱為本,但覺與迷時,性不能合耳。茲舉喻以明,如明珠兩顆,一本潔淨,一塗垢塵,淨者光自顯,垢者光自隱,顯者光未增,隱者光未減,雖不增減,光不能交,似淨者自淨,垢者自垢,如去其垢,兩光不分。
問:眾生與佛之性是否一體?若一體,豈有佛覺而眾生未覺?(蔡榮華)
答:在鑛之金,與朔望之月,同金同月,並無二致。試思在鑛之金,與成器之金,不皆曰金乎。並非在鑛是鐵,成器曰金。朔日之月,與望日之月,不皆是月乎。亦非朔日謂影,望日是月。此金與月,即喻於性,佛之性去盡纏蓋,猶成器之金,望滿之月,凡眾性在纏蓋,猶金在鑛,如月處晦耳。性德本覺本明,既從無始無明,故必假修德,始得漸次圓明也。
問:學佛淺說一書首頁云「我們的本來面目,在那無始以前無明未動的時候,原是不死不生,與佛的心性一樣,因為無明一動,就鑽進了生死的圈子。」無明有始抑無始?其言「無明一動」是其有始乎?若言無始是否吾輩不知其始,故言無始?(蔡榮華)
答:此不過形容性為本覺,為人易了而言,行文之間,少嫌簡略而已。實則性之本體,原是如如光明,却從無始動被無明。簡言之,性原理不動,而從來即動,雖動而不失其不動,其不動方是其真。如水性非流,而水無不流,雖流而非水之本,不流方是水真。若不悟性無始而動,請研究水何時始流。至於末四句,追求「不知」與「故言」,曰非故言,吾輩亦實不知。
問:非有非空,即有即空,僧肇有言「離四句遣百非」,其義蘊安在?(張瑞良)
答:覺性說有說空,皆偏而不圓,不符真際實。則空含妙有,有本真空。經曰: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。」則是空有不二,其妙處在是,不可思,曰心行處滅 ,不可議,曰言語道斷,夫如是,安有四句百非。
問:何以人死而佛性不滅?(趙哲)
答:貴居士所言之人,肉身之形也,猶如人家電燈之泡,日光燈之筒,佛性如電廠電力也。試問人家燈泡及燈筒壞後,電廠之電力滅乎?
問:佛性是否就是真如(真心)?(趙哲)
答:佛性無形而有靈,以其常而不滅,故名曰「真如」,亦曰「真心」。
問:楞嚴經:「見見之時,見非是見,見猶離見,見不能及」求師重講一遍。(慧之)
答:「見見之時」第一見指本體能照之真見,第二見指帶無明之妄見。「見非是見」第一見與上句第一字同,第四見與上句第二字同。合講即真見常為妄蔽,全真成妄,若真能起照,照見妄見之時,則真見即不為妄見所蔽,全妄成真矣。「見猶離見」、「見不能及」二句,第一見指真,二三皆是指妄。合講真見本性妄想幻想,真離妄時,真性本空,妄無所依,幻相亦空,此四古德各有釋義,並皆精妙,今之所答,不過一義而已。
問:人人之佛性本來清淨,何以會起無明?成佛之後也是返復清淨之佛性,那時是否會再起無明?(蔡慈心)
答:性本清淨光明,忽求加明,此之一動,翻成無明,此後三細六粗,迷上加迷。此性所以如是者,猶金在鑛,未經冶提,不成純金。倘加提煉,去鑛存金,是已精純,以後自不再化鑛沙,覺後成佛,亦猶是也。
問:坐功至「靈靈不昧,了了常知」,攀緣心是否已息,如屬已息,這種常知之心,是否即屬「性」也?(吳任輝)
答:「靈靈不昧,了了常知」屬慧。攀緣心息、屬定,行人必定慧平均,方為正受,可云攀緣心息。如偏一方,息與不息,尚難遽斷,惟定與慧,皆屬性有。
問:東坡「溪聲盡是廣長舌」是否見性後境界?(潔園)
答:東坡此二句,可謂悟語,然悟亦有大小,悟與證不同,故二句後人有贊有毀。見性與否,區區難斷,蓋見性人方知見性人,否則不識廬山真面。
問:「即有之空」是否指一切法生滅不停,「即空之有」可否作真空妙有解?(潔園)
答:「即有之空」是隨緣不變。「即空之有」是不變隨緣,都云「真空妙有」庶乎可,若「生滅不停」則過矣。
問:經云:「若不觀心法無來處」,是否自性能生萬法之理?(潔園)
答:心生則萬法生,心滅則萬法滅,真實不虛,真實不虛。初機聞之茫然,深研自然澈了。
問:曾見有解「對境無心」,稱與儒之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」和金經「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」相同,竊意金經稱性而談,儒之心不在焉似識心猶在,是否可以相提並論?(潔園)
答:此二說乃各有因而言,不可相提並論。金經所言,教人就相悟體,儒家所言數句,只言事不專心,雖對境亦不知耳。
問:水態三變化。氣體、液體、固體是體相,三者有共同的溼性,不因其相體變化而變化,那個能變化的(氣、液、固之相),有如眾生六道輪迴,而不變化的(溼性),有如眾生都有佛性。又真如實性,本來面目,妙覺真心,是否皆屬佛性的異名?(高國範)
答:如是如是。
問:性必寄動物而存嗎?了生脫死是否是性不再託於動物?即曰性皆具智慧德能,而動物皆各有性,何以其他動物無佛性?人與動物有何區別?(姜其蘭)
答:動物者,生物之謂也,有生即有死,性寄動物,即是生死不了,不寄動物,自是不生,不生即不滅,此名了生脫死也。性具智慧德能,但為三惑所障,而不能顯,惑斷即顯也。斷惑顯性之法,在於「聞思修」三慧,任何動物,皆有佛性,不過人於三慧機緣多,故顯性較易,他動物於三慧機緣少,故顯性不易耳。
問:既言「永遠存在者唯本性」,又言「本性為真空,非物質。」我不懂既是真空,以何「相」求永遠存在?(陳春份)
答:性無有相,若有相者,皆是因緣合和,而非其本體。性有而言空者,乃言空無物質,空無現象,故曰真空。喻影雖無物質,尚有現象,故不曰真空,性雖無相,而法由之生起,故雖空而實有。悟此者,非久學之士而不能,初學不明,不足怪也。
問:學佛為求「性」之真自由,達了生脫死之目的。「性」是否吾人能體會得,如果有人能修得輕安自在心,是否其「性」得到解脫?(陳春份)
答:性為人人皆有,箇箇不無,誰修誰證,不修不證,此非佛教一家之言,孔子孟子皆言性,漢儒以至各儒,亦皆言性。今日之學,絕不談此,故聽之茫然,研求則能證之。所云輕者安,不過求明心見性之初步,離解脫尚遠之遠矣。
問:孟子性善,荀子性惡,告子不善不惡,到底是善抑惡、亦善亦惡、不善不惡?(張文榮)
答:言性之學,非文學家事,是此非彼,各執其執。彼等既為孔子之徒,所讀性理而與孔子所說皆不合也。孔子所言,相近習遠,昭昭在書,各家似未領會。子貢乃孔子高足,尚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,可見性之難言,足徵後儒所言皆逞己見,不師於孔子,亦無體驗之功夫。但來問所提四端,乃性體之隨緣,而非性不受之本體,而此本體惟佛一人知之,餘皆相似,應知言善言惡,皆是相對而有,並非絕對,故知凡有言說,都無是處也。般若性空,試觀於空,是善是惡,抑不善不惡,亦善亦惡耶。性心意識,如不能分,直等指鹿為馬,呼雞作鳳而已。
問:宇宙間,是否存有絕對論?(張文榮)
答:居士正在求學初機,此等問題,大哲學家、大科學家,尚不能決,何可居卑言高。雖不恥下問,但區區心亦塞茅,何能知之。惟曾研佛學,嘗聞般若,得知妙明覺性,非因緣有,非自然生,只有一乘,無二無三,而又不與萬法共,是真絕對矣。
問:無修、無證之佛,是怎麼有的?(林金)
答:無修無證之佛,指真性也。萬法皆為因緣所生,惟性獨非,生者有相,無生真空,若問佛性是怎麼有,試思空是怎麼有,便解決矣。
問:德山大師(周金剛)之言「一毛吞海,性無虧。纖芥投鋒,鋒利不動。學與無學,惟我知焉」?(林金)
答:一毛吞海,纖芥投鋒之語,德山大師,曾言之矣,「學與無學,惟我知焉。」無學乃羅漢果,學乃一二三等果,彼等尚且不知,區區半果也無,子偏來問,倘有所說,豈非以盲引盲,大大不可。
問:諦閑大師云:「諸法之相,惟心所現。法無自性,以心為體。一切眾生,同共一如來藏心,相雖各異,體實平等」云云。後學不明「一切眾生,共同一如來藏心」一句。眾生甚多,一一眾生各有一心,何謂「同共一心」?乞舉例明之。(趙哲)
答:動物雖賴飲食而活,尚有不可須臾離之空氣,此空氣得之則生,閉之則死,既知此氣重要,即以空氣為喻可也。試思空氣,何地無之。熱帶者則熱,寒帶者則寒,鮑魚肆氣則臭,芝蘭室氣則芬,而此四處,各有多數動物吸之。此大空氣是一是多,若明比喻,共同一如來藏可以悟矣。
問:楞嚴經說「聞性是常」這道理我不明白,六根都不常,為什麼聞性常呢?(謝幼)
答:性本真常,不生不滅,根塵識三,皆性幻生。幻生者,自然幻滅,常者自常,幻者自滅,其理易知,無難解處。或所誤者,聞性一名,應知聞性,仍是本性,並非耳根之中,另一聞性,故根滅而性仍存。
問:斷見為佛家所非,故愣嚴中有發顯神識離體獨立之說,謂神識雖托體顯用,然其自身實不隨肉體以俱滅也。關於此點,若以電喻神識,鎢絲喻肉體,則鎢絲雖斷滅不能發光,而電未嘗滅,斯喻無過。若以電喻神識,乾電池之種種物質喻肉體,則乾電池之物質銷亡,電亦不存,推知肉體識神二同時滅,而斷滅之見得以成立。是知譬喻之難,非率爾可就,佛經之中譬喻甚多,果真全然切當耶。如楞嚴以金礦喻本性,心假修鍊始得精純。可知本性原非清淨,何得謂為本來清淨。因一念不覺,而有無明哉。(正如金礦豈因不覺而雜沙石 ,實在本來已雜沙石矣),如是則一念不覺有無明,無明為因生三細,等俱不成立。復次即令性原清淨,則如其金一純,更不成雜,亦無一念不覺之可言,更無塵沙見思等,總之斷滅之見,本性清淨,與及一念不覺等說,譬喻之切當與否,疑點甚多,請就以上所言詳釋其惑?(李蓮階)
答:譬喻非真,僅得彷彿,前已言之,在推不在執。茲忽提出肉體識神同滅,承認斷見,誤會重重,去題更遠。應先明性,而非識神,此亦易解權說,實則萬法皆性,無相者真而不變,有相者幻而隨緣。性空不變,識相隨緣,肉體亦相,諸相幻變,假說為滅,而實不生。次說金鍊始純,疑性原非清淨。應知金小,雖如兔毛之塵,鑛土縱大,如丘如陵,是鑛掩金,非金與鑛合,金仍純金,鍊去塵非鍊金也。三謂如金一純,自無一念不覺。亦無三細,更無塵沙見思。應知無明非性,乃障性之事。一念無明者,如金粒染鑛土,生三細者,如土生苔蘚之類,塵沙見惑,如山石草木等類,雖掩金者,有種種雜物,然鑛中之金粒,非生諸物之體也。
問:經中常云:「是心是佛,是心作佛,唯心淨土,自性彌陀」。此「心」與「性」之區別安在?佛者覺悟,是覺悟心耶或性耶?(鄭朝信)
答:諸經心性二字,有時有處,心性不作二解,說性即是說心。如本條所問,是心是佛等四句者是。易於時處,則心性各解,如唯識家,八識皆稱曰心,諸心俱是幻妄,轉識成智,則復本性,性無妄性,則是二名區別。若言其覺,只有權答,真如本性,性自「本覺」,心有幻妄,心有「始覺」。
問:實相者,真實之相,平等之相,諸法雖有生滅,然於生滅之中有不生滅性,此諸法是否包括有情與無情,若無情則物壞了,消失了,那有不生滅性?(鄭志西)
答:實相簡單講,即謂「不生滅性」。此性本空,而無所相,指此真空惟實,強曰實相,若明此理,實無有相。金剛經曰「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」。可悟實相無相,情與無情,森羅萬象,皆是妄念幻有,現此幻相,電影銀幕之上,有相無質,光射在銀幕時,幕上實無物生,光停射銀幕時,幕上實無物滅,情與無情,事亦如之,生則實無所生,滅亦實不滅。再相由心生,實事如是,居士言「物壞了,消失了,那有不生滅性。」似誤為性由相生矣。
問:佛與眾生性,為同為別?(鄭志西)
答:性本無別,所少異者,一為在纏,一為出纏耳。
問:真性是無形,何能染污?(池慧霖)
答:染污二字,即是不清淨而已。性雖無形,非無其性,試思見聞覺知有形乎。收視返聽有形乎,固知無形,然能見聞覺知乎,能收視返聽乎?見聞與收視等是何物也。當見聞覺知時,即是染也,當收視返聽時,即是淨也。
問:心不自心因境而有,境不自境由心而生,如何解呢?(鄭勝陽)
答:心謂心念也,不自心,謂念不自起。境謂六塵,及一切染淨諸境也。合言之,即念起因觸境而起也。所謂「心本不生因境有」,然則境從何來,而境又實從心出,因一念不覺,而有「業相」,繼生「見相」,見必求對,則「境相」造出矣。此名「無明為因生三細」。又曰「萬法唯心造」。此後則引境妄念,妄念造境,互依為非,狼狽為奸,生死相續,無有終期矣。
問:一元的、十方諸佛之真如本性,如大海水融為一體,無二無別,眾生成佛,猶如細流,歸入大海,與十方佛,融合為一。多元的,十方諸佛之真如本性,如摩尼珠,性質雖同,各有其體,眾生成佛,猶如垢珠,去垢復明,與十方佛,似一各別?(無名氏)
答:此二疑可合併論之。二疑之中,俱謂「眾生成佛」。成佛始能如水流合水流,珠光合珠光,不成則不能合之。不能合時,「似一各別」。融一體時,「融合為一」。
問:老師講金剛經時對「如來者即諸法如義」解釋云:即萬法一如。弟子尚未悟得,似覺兩者尚不盡相同,乞再予開示。(鮮純贊)
答:佛理至深,實語、如語、真語、不妄不誑。「如來諸法如義」者,如來即是真心,「一切惟心造」,一切者諸法也,心造諸法,法寧非心。心體真空,法相假色,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,豈非一如。若言未悟,語並無過,只有思維,時時靜參。倘說「似覺兩者尚不盡同」則是謗法,不信於佛矣。
問:言語道斷,心行處滅,何解?(志西)
答:學佛誓在成佛,成佛必求見性,千經萬論,雖多說性,只是善巧方便,解釋譬喻,引人參悟,自證方得,真性之體,非言能說,即用意想,便是錯誤。故曰「言語道斷,心行處滅」。大致謂言語不能說,意念不能到,亦可謂口至無可為言,心至無念而起,則靈光獨耀,真性見矣。
問:高級佛學教本第卅四、五、六課綜合指要第十一節,即是最末尾一節「極樂國的一切依正,及其動作,只是一個大夢境,大幻術,實際上是一無所有,有如太空。」末學不明此義。(鍾雲昌)
答:所謂高級佛學者,便知非初學能解,因恐誤會,故不憚煩瑣為言。功夫有漸有頓,漸則必依次第,即所謂三諦三觀也。初修從有入「空」,是謂「真」觀,證「一切智」。再則從空出「假」,是謂「有」觀,證「道種智」。後則雙遮雙照,不偏空有,是謂「中」觀,證一切種智 。中道者,是諸法實相,此實相即真如,即是佛性,即是佛土。實相之義有三:一、無相之實相,即無妄相,合於空諦。二、無不相之實相,即隨緣現色,合於假諦。三、無相無不相,真空妙有,即而不離,合於中諦。極樂佛土,即真如佛性,亦是實相,以其無相無不相,故現「寂光」、「實報」、「方便」、「同居」四相,前一是真如不變,後三是真如隨緣,非一非四,非空非有。彼一課本,言夢幻者,指其隨緣之相,而言太空者,指其不變之相。
問:夢裡明明有六趣,覺後空空無大千,此義亦不詳細。(鍾雲昌)
答:六趣有情,大千器界,皆是眾緣和合,而生其相。迷者不知,認為真實,為所顛倒,故曰「夢裡明明有六趣」。悟者照見,諸相皆幻,空無自體,故曰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。對於此義,既言不詳,茲答亦恐誤會,宜參考前條「實相」之說,可以了然。
問:金剛經四句偈內有「以音聲求我」句,未知至何等程度即能不求可得?(陳寬鳳)
答:若到四相不著,能所兩亡,即是相當程度。若至無智無得,空有皆空,即是不求而得。
問:真如自性不垢不染本自清淨,既能自然而生,現在山河大地,無明眾生,將來眾生儘皆成佛之後,經若干劫豈不是仍然與現在一樣會生山河大地無明眾生等事物 ?(李明揚)
答:本性本自清淨,本指本體,謂真體之中,無垢無染,然無始以來,而有無明,故體不垢似垢,不染似染,此舉喻,方易了解,金本光明,中無垢染,而出鑛中與塵沙混,實則塵沙附其上,非金內有塵沙也,是金無塵沙,似有塵沙。金被塵蒙,則現妄形,性遮無明,則現妄象,其理本同。祖云「夢裡明明有六趣,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亦此事也。修行人所修者,去性附之無明,非修性之本體,無明去本性顯,即是佛矣。智與能皆性本具,故經云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冶金者但去其沙,金即純矣,光色實非從冶來也,金既成器,不再變鑛,無明性覺,不再入迷,其理一也。
問:眾生最初原具佛性清淨,即原來眾生都是佛。既然是佛了,為什麼會染無明,而淪入六道輪廻?(周敏雄)
答:說義辭費而難明,不如借物喻之。○圓圈符號代佛性,喻如鑛中之金,圈中黑點符號代無明,喻如金藏礦中,然有礦方有金,有金始名礦,金與礦同時互有,分則二物。本來佛性,無始即有無明,細觀之性只是性,無明只是無明,兩種既不相入,更不混而為一,不過無明起相,遮隱本性而已。如礦能隱金,金卻不為礦入,一旦熔冶,礦去金存,不經熔冶,金不能顯。眾生雖具性德,必假修德,方顯本來面目,而得解脫。
問:如果說本來就是染污,我們如何知道污點是可以去掉,我們何不說清淨是對外求得的?(周敏雄)
答:○表性之淨分,圈中有黑點者表性之染分,淨染各有力,淨染互不能融,淨有覺力能破染,染有迷力能隱淨,倘得外緣為助,覺得之則能破染,迷得之更能隱淨。上僅就外緣而論,若從根本上說,性染無明,亦有輕重萬別,染輕者遇事而覺,不待佛法。染重者遇事增迷,不待五欲。
問:圓瑛法師註楞嚴經講義一○八頁「佛破無處是欲其了悟無體非心矣」,究屬何義?(李蓮階)
答:試想虛空拘於一處否?何處而非虛空,如限虛空有處,事理皆錯。心則盡包虛空,空含心中,猶如片雲,而點太空,空尚不能限處,心焉能限於一處。
問:講義一一七頁「此經宗要即是捨識用根」,請問如何是捨識用根?又三七頁云「開道眼是心智眼非勝義眼根可比」,則眼根不及道眼明矣,何不捨識開道眼而要捨識用眼根(眼根是六根之一,捨識用眼根,自可含於捨識用根之內)?(李蓮階)
答:此問分二。一、捨識用根,各家主張不同,茲置不論,但就圓師所註答之。識即意識,根謂根性,即經文之「識精元明」,註義謂剷除意識,專守真常也。二、此處所云之道眼,非六根之眼,乃借以指心,因眼明方能見物,喻心明始能知道也。
問:講義一二九頁「識性虛妄故名妄想,根性真常故稱佛性」祈示,根是否有性?如有性是何性?因何而有?與本性是一是二?據唯識簡介識原於性,性三變而為六識,六識依根塵而生 ,則根為識之依緣而已,連識且不及,何比於本性?如吾人以錢市物應用物而設(姑喻識原於性),物依錢而買(識依根生),錢與用不能混為一談,則根與本性自是兩樣 ,本性真常固無疑義,根性真常又作何解?(李蓮階)
答:可參第二問答,此講義所云之根,非是六根之根,根者自也,根者本有也。係形容辭,非物質名,如云根本煩惱、根本智等。根性即本性,一事二名也,既知說性,餘疑可解。
問:六祖惠能大師畫傳第三十三頁的三十一是非障道,此題中「大師又說,我此法門,既不著心,亦不著淨,亦非不動……」其是亦不著淨或亦不著靜呢?(陳鵬)
答:此係教勘問題,是種畫傳,區區未曾寓目,恐非古本,今人排版,出錯乃其常事。至所引六祖之言,亦未指出何典,手中無書可考,未敢武斷。按淨與靜,兩者皆合文理,淨字與句中之心有關,靜字與句中之動有關。必看原書上下聯文,及對照善本書,依據而言,始無過錯。
問:惠能大師說,蓋一切塵勞妄想,皆從念生也。那麼淨土宗專念阿彌陀佛亦是在打妄想啊?何解呢?(陳鵬)
答:塵勞乃貪瞋煩惱之異名,塵染六根,勞亂身心之意。妄想者,虛妄分別之雜念,使不能定,有造作業苦之能。阿彌陀佛,乃極果之淨聖,真常之性德,寂光之法身,大圓鏡普照之智,融解脫法身般若無相德體,若念之,則念茲在茲,心念心是,心即是佛,作如是解。若一味儱侗,有念皆指為妄,試思六祖說「菩提本無樹」達摩曰「一花開五葉,結果自然成。」世尊四九說法,各有念乎。無念何能說,有念是妄乎。寧知念有妄,殊不知尚有淨有正乎。經曰「淨念相繼」。大珠和尚曰「無念者,無妄念,非無正念也。」再隨煩惱中有「失念」一項,亦請思作何解釋。
問:學道者,證得法身時,是證到釋迦牟尼佛的法身,或是阿彌陀佛的法身,或是自己的法身,或抑與諸佛共一身?(張嘉南)
答:自然是證得自己之法身,證得法身,即是佛身,經訓云「十方三世佛,共同一法身。」以此理視之法身有別而無別,既與諸佛同身,釋迦彌陀,豈在例外。
問:眾生自無始以來本具,何以會因一念不覺而入六道,而由修成佛後,即永不會再迷而入六道輪迴?(翁忠行)
答:君以事問,希以理答,理答義繁,莫若喻解。金在礦中,自然與塵沙相混,金喻佛性,塵沙則喻無明不覺。倘經採而冶煉成器,則永離塵沙。金器喻已成佛果,永離塵沙,喻不復再迷。
問:眾生與佛,法身既本是一體,如何會有各個差別之相?(焦國寶)
答:說理費解,舉譬易解。寺廟之佛像,堂階之鐘鏞,几上之鼎彝,竈中之釜錡,閨中之燈鏡,馬身之勒鐙,其相不一,貴賤有異。然其體皆係金質,並無不同,如易其相,貴者可做賤物,賤者亦可改造貴品,是差別者相耳,體則實無有二。
問:眾生皆有佛性,無始以來不覺生情造罪演出生死輪迴不停,既然眾生的佛性是本有不是外來,然追其最早一因,不覺墮落是從那裡來的?是否從佛而來的?(李松麟)
答:性為無始而有,中國文化,亦曰天命之謂性,天命亦是無始,此節應先了知。來問既曰「無始以來不覺」是已經自問自答矣。以不覺即是無明,此如金體與礦土同生同處,金體雖掩土內,不見光明,然金實不為土損,本性與無明同有,性雖無明遮蓋,然性終不為滅。金體必經鎔冶,礦土始去,本性必經修持,無明始斷也。初機只應粗知,詳解須待後緣。
問:本性與神識如何分別?(謝幼)
答:真空無相,清淨光明,一念不生,如如不動,這是本性。一念不覺,而有無明,能所分明,攀緣不已,變為神識。本性比水,神識比波,本是一事,動靜有異耳。
問:萬法唯心造,此心是否即是念頭?(王心普)
答:心造之心即指念頭而言。
問:心之體是否即是性,心之相是否即是念?(王心普)
答:唯識家心與性,分而言之,禪家心與性,合一言之。聽之似有不同,然在解釋上,則無不一也。再心原無相,強言則曰實相,如言念是心相,自無不可。古德云,當前一念,或曰正念,或曰淨念,曾稱真心,今名心相,似較真心尤佳。蓋念本無體 ,亦屬空法,空尚稱相,念何不可稱相耶。
問:體相不可離,故一切凡聖皆不離乎念,不知然否?(王心普)
答:體表於相,相依乎體,為方便計,故假言說。是一非一,是二非二,亦即亦離,不即不離。此等事理,在參在修,所謂言語道斷,心行處滅也。至於凡夫之相,固不離念,若言大聖境界,則是離念靈知,亦曰寂而常知,靈知常照,不云乎念。
問:雜亂之念即是妄念,定於一即為正念,著於相即為染,不著相即為淨,染則受繫缚,淨則得解脫,此解是否正確?(王心普)
答:所發之言,尚屬正知正見,惟「定於一」句,應加注意,所謂一者,必依無漏法也。
問:王陽明究竟話頭無善無惡心之體,是指其真如佛性,有善有惡意之動,指一念妄動,成為某識,故有善惡分別,即令王陽明並未證到心體雜念境界,但此話對否?(何毅生)
答:陽明先生,所言之性,較孟告荀楊等,均為精粹,能界體用靜動分析,自不似前人儱侗。宋明儒家言性之語,少成理者,多陰襲佛說,陽明其一也。後來者居上,聞之多見之廣,勢所然也。
問:與某師談孟子性善說,余謂真如具萬善性德大用故性善,論荀子性惡,余謂就眾生無明業識,與生俱來,故性惡說亦對,並舉嬰兒知貪瞋愛取為例,未知有違佛理否?(何毅生)
答:善惡者,相對而非絕對,如如不動,無所謂善惡,此主清淨妙心之一說。亦有主性與無明,皆為無始而有,如金在礦。此二佛家皆有之。然說雖有二,實則性自性,無明自無明,不過礦金互依,交互似一,事則金自金,礦自礦耳。無明依性,性起無明,亦似一非一。既曰出纏,又曰解脫,若果是一,何有出與解脫耶。孟荀所言,雖各中其一,然思維皆不及此,觀二家所論舉例,孩提嬰兒之相,早與性離去萬億兆層,故知其偶中,而非真知也。
問:何謂明心見性?(張豁然)
答:先說心性二字,此二各家主張,並不相同,止觀大意,謂「不變隨緣故為心,隨緣不變故為性。」禪宗則謂之同。黃檗傳心法要「心性不異」。眾生心性,為無明障遮,若澈悟破迷,即是明心,斷惑顯真,即是見性。
問:二乘聖人既已斷見思惑,理應明自本心,何以涅槃經云其有不見佛性者,長者見地,不妨施沾下愚?(張豁然)
答:三德佛性,法身般若解脫,乃涅槃之秘藏,三而一者也。法身為佛本體,即是法性,阿羅漢雖斷見思,只得一半解脫,般若及法身,皆未證也。惑有見思塵沙元品無明,阿羅漢僅斷見思,餘皆存在也。
問:正當妄念瞥起,一照之下即消失,此時如何見性?(張豁然)
答:此是觀,非是悟,初步功夫,云何見性。冒昧忠告,修學者,或宗或教,或禪或淨,乃今日之通途,然必一門深入,餘作助緣。任何一途,必有師承,閉門造車,未必合轍。總觀數次所問,亦可略知台端境界,「教」、「禪」、「淨」三,皆未求師,亦未訪問知識。雖曰十有餘年,似屬唐捐,不得入處,大概受貢高之障。徒有好道之心,惜未遇助道之緣,前途之果,便茫茫矣。「教」須先通一經,澈頭澈尾,了解明白。「禪」須求師指點,放下一切,起疑真參實悟。「淨」亦如此,必真信切願,一心直念。解應多看,行必在一。經訓「因地不真,果招紆曲。」古德曾云,學必正知正見,否則驢年方成。
問:眾生原本皆具佛性,只因「無始」來造業而至今之地步,是否在「無始」前,眾生亦具清淨之心,即同佛一樣?(王允右)
答:無始者,無能得其始也,覓始尚無,何能覓始之前。至云,眾生皆具佛性,是言此性,現乃佛因,後能成果。修則成之,不修則否,以佛而言,並非自然釋迦,天生彌陀,亦係福慧雙行,三祇修來。
問:心佛眾生三無差別,心是心、佛是佛、眾生是眾生,為何說三無差別?(蕭慧心)
答:佛亦此心,眾亦此心,心迷即眾生,心覺即佛陀。三者乃一體變化,從本而論,皆是心法,故曰三無差別。
問:靈光獨耀,是指吾人之真如本性,在破除三惑以後,雖是清淨寂滅如如不動,無任何跡相可尋,但是他的靈明不昧的知覺力則完滿無缺,故曰靈光獨耀,此光並非與日月燈光之照相似,然否?(鮮純賢)
答:此本二句,靈光與根塵,凡學佛人,大率能知,其所重者,在「獨耀」與「迥脫」四字。且勿取櫝還珠,向名相上纏繞葛藤,拆兩講一,義亦不達。
問:請示有情無情同圓種智?(焦國寶)
答:此一問題答之屢屢,皆載於正續問答編中,希查。再為言之,有情者皆知,置之不論,專談無情。極樂寶樹羅網,池水花香,皆是無情,可以說法。蓮花樓閣,飲食衣服,皆是無情,或聞佛聲而生,或應人念起至,既解聞法,又能說法,安得不圓種智。如謂極樂無情,乃彌陀所化,豈不聞此土飛花落葉,磚石瓦礫,熾然說法。雨花盈臺,頑石點頭,皆得法悅,非亦能說能聞乎。經論皆云,有情無情,皆有其性,此性法佛一如,圓智豈異。
問:請釋「生死即涅槃」、「煩惱即菩提」?(焦國寶)
答:生死涅槃如醒睡,醒睡是汝心狀態,心體不曾有醒睡。煩惱菩提如晝夜,晝夜是空妄象,虛空不曾有晝夜。
問:心佛眾生三無差別,以弟子思維真心即佛,妄心即眾生,真妄似有差別?(鮮純賢)
答:迷即謂妄,覺即謂真。迷亦有深淺之別,覺更有始竟不同,寂照謂真,動念謂妄,然寂照動念,常暫頻偶,亦非一致,此皆差別大略也。妄惑未全斷淨,仍不究竟,故登地菩薩,亦稱眾生,初發心修,一惑未斷,因有真性,亦名字佛。
問:對無始二字可否作如下之方便解說。佛學上所謂的「無始」實在是有始,不過因開始的時間在久遠劫,而當時並無與現在相同之曆算與文字,無法記述而已,如經云「知見立知即無明本」、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等 ,在「立知」與「不覺」時就是迷惑開始了,眾生迷了本性以後,即輪迴六道,如環之無端,本身自無記憶能力,所以只好稱為無始。然否?(鮮純賢)
答:尊論「立知」、「不覺」就是無明,或謂是無明一段之開始,區區並無異議。若無一段二字,直謂「立知」、「不覺」,便是開始,則不敢苟同。試問「立知」、「不覺」從何而來,能謂無因而生乎。細玩緣生論,無此義理。開始者,乃事理之生,生相即一段之果,果必有其因,既前有因,何可謂後果是開始。
問:上次師云「佛根本沒有生也沒有死」弟子參得法身佛,如如不動本無生死,若以釋迦佛在印度降生之化身而言,是隨緣現相可以說有生死然否?(鮮純賢)
答:昔言佛者,言心體即佛也,以其別於肉身之假相,故言沒有生死。若印度化身假相,雖現滅相,滅者只身相,非心體也。
問:師令弟子參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色空原是本性迷了,由見分求見而引起之虛幻境相,無是非可言,不過為契眾生機,則方便說色是緣生性空,空又是真空妙有,隨緣現諸色,故說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然否?(鮮純賢)
答: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乃是真說,非方便也。
問:所謂六根清淨有云是六根對塵境全不知覺之謂,有云是塵根對境雖知覺但不攀緣之謂,二者誰是正確講法?(鮮純賢)
答:前者非,後者是,但說不圓融,若不攀緣,是有目不看,有耳不聽。佛與祖坐道場時,大眾聚俱,豈是不看不聽。不過如鏡鑒物,胡來胡現,漢來漢現,胡漢去而鏡空無跡,胡漢現時,而鏡亦不為所染而已,此之謂清淨。
問:六祖云「世人妙性本空……自性真空……」又云「若空心靜坐,即著無記空」,請問「妙性本空」與空心靜坐之「空心」有何不同?空心靜坐,為何不合理法,而有著無記空之嫌。不是空心靜坐,難道還要有什麼事實之心來靜坐嗎?(高瞻)
答:「妙性本空」句,與「空心靜坐」句,原為兩事,不能合併比較。「妙性本空」是研性理,乃說萬法雖為性造,而性即真如實體異名,空無有相故稱為妙。「空心靜坐」乃是習定用功,定在靜慮,不在靜形,應無妄念,非無正念。若無正念,即是頑空。
問:圓覺經云「不二隨順」,不知怎解?(高瞻)
答:解答此欄者,如求一熟記三藏之人,今或有之,我未見也。在下不過隨緣隨分,答曾見聞尚未忘者,如已忘矣,必須查對上下之文,倘就句答句,必害經義。若孟子「左右皆曰可殺,勿聽。」只就此問答,有被殺者,向警報案,警可推而不理乎。凡問經書,例須說明品名某處,或其每段,以便答者易查,禹寸陶分,不使浪費時間也。圓覺經文甚短,在下閑時亦甚短,乞諒。
問:信仰宗教之目的皆為要得精神解脫(即是能解脫死亡之困苦)。佛經所說人人有佛性,而人人不自覺知,此項說明以本身自己體驗信為千真萬確。「當離見聞覺知時尚有物存在者即是佛性。」此語為方倫居士在「禪話與淨話」裡所說。當人們熟睡無一點知覺時,佛性(第八識阿賴耶識)確還在腦中,執著生命,所以人們還不死。即是我們不自覺,但確有在腦裡有第八識之存在。但當人們死時該第八識諒已不存在於腦中吧。(即醫學上謂瞳孔散大才確定死)那麼人們死時,第八識即阿賴耶識(佛性)跑到那裡去了。佛性已非物質,非能移動或跑動之物,或佛性,人死時就消失在腦中呢。那麼佛經所說之「佛性不生不滅」之真義為何?(鄭剛毅)
答:首先聲明,先生議論雖多,有質問處,方與答復。有錯誤處,為注誤解二字,但不與加解,誤之深,解之淺,反更加誤會也。貴論「第八識阿賴耶識確還在腦中」誤解。凡夫之性,為煩惱纏缚,牽引流動,即名來去。十法界中,有六種凡夫,在纏之性,為善惡惑業牽引,投入和合成胎,(八識規矩頌)偈曰「先來後去作主公」是其來去也。在六道中,死此生彼,輪迴不斷,是其不滅也。偈曰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,未見佛及未見性者,不能理解無生也。
問:在佛經上諒未提起此宇宙之原始因為何?宇宙萬物不離因果,那麼宇宙之原始因為何,才有今天之結果?(鄭剛毅)
答:三藏經典,無非說明宇宙萬有,轉移宇宙萬有,不但說其原始,而且說到無始。若問「原始因為何」。說錯話不過幾句,說實話,皆在三藏內。佛尚說了四十九年,還有人聽不懂,懂而大悟證果,不懂仍在輪迴。先生果真求道,三藏浩浩,諒難研究,最低限度,須讀明白一本起信論,方有個入處。本人在短時間,只能說句儱侗話,萬法唯心造,宇宙是妄心所現。
問:當人們將要死時神識(佛性)是否能投胎及以如何方式投胎呢?(鄭剛毅)
答:投胎者,第八識向六道中投胎。六道者,為天、人、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也。可怕者,此六道生死,彼此來往,作善者,投天人修羅,作惡者,投畜生餓鬼地獄,業力所牽,概不由己也。此即第一答之來往,亦即不滅也,此僅略說大概,看經方能詳知。
問:毗盧遮那是法身佛,此佛唯是釋迦世尊之法身,抑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法身?(劍老居士)
答:性德修德,圓滿以後,是謂之佛,其體相用隨緣利眾,名分三身,曰法報應。真如即法身,梵語「毘盧遮那」,義為遍一切處。十方三世之佛,皆具三身,不獨釋迦世尊也。
問:心佛眾生既三無差別,如為一,佛眾生亦然,如為諸佛眾生亦爾,何故不許毗盧為眾生之法身,法身之名尚不得稱一,豈有二耶?(劍老居士)
答:心為主體,迷則眾生,覺則稱佛,名依變異而呼,實則名三事一,故曰無差別也。以心無可形容,且具萬法,不生不滅,故稱真如。但被無明遮障,是謂在纏如來,迨無明盡,即稱法身。眾生皆有佛性一語,人所共知,佛性即心,即法身也。不過在纏未顯,還是積聚業報之身耳。
問:法身無為不墮諸數,是則毗盧之名,雖係強加,不亦同蛇足乎?(劍老居士)
答:真如無相無為,可參難言,故有「言語道斷,心行處滅」之語。雖則如此,但佛家了義之法,即在明心見性,教典稱為內學,端在此點。如因「言語道斷」則不言,何以度眾。勢必宣說,方盡悲心。故在無可如何之下,強加假名,俾人因指見月,指非多此一舉,強名亦不得已於言也。
問:華藏世界之外,是否另有無量世界,而東方琉璃,西方極樂,上方兜率,是否全在華藏包涵之內?(劍老居士)
答:華藏世界,乃諸佛報土之通名,華嚴經所言之華藏,為釋迦如來之華藏也。經載上下二十重,周圍十一周,十一周外,仍有世界。古德曾繪有華藏略圖,極樂列入第十三重(數記不清),兜率乃娑婆之範圍,當然包涵其中。
問:過去佛已俱入涅槃,未知此涅槃諸佛亦仍分身塵剎度眾生否?如其仍度,則不得謂之過去,如已不度則不失慈心乎?(劍老居士)
答:佛度眾生,並無休息,以釋迦世尊而言,經載化身來入娑婆,已八千次,他佛可知。稱過去者,以每一度數而言,隨緣而來,謂之現在,緣盡他逝,謂之過去,以應化身論,不以法身論也。茲設喻以明之。法身如日光,應化如日影,地球私轉一周,日光射影於地對處,謂之晝,背處不射日影,謂之夜。若地球再轉一周,則與明暗一次,稱今日昨日矣,實則影之射到與否,權稱過去現在,而日光何嘗有息滅耶。
問:有心有識方可轉而成佛,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,磚瓦竹石皆無心之物,何以亦得成佛,若謂依隨正轉,如俗所謂拔宅飛昇或雞犬俱生之類,而極樂世界之種種莊嚴又何以云皆是彌陀變化所作,而不言是無情成佛耶?(劍老居士)
答:此一問題,十數年來,問之屢屢,答亦頻頻,然問雖不異,答卻多方。因義深奧不一其義,而昔年所答,不可不參。其理為心乃「一真法界」。「心如工畫師,造種種五陰。」即山河大地,皆為心體所幻妄相,由識分別,而現種種塵境,若轉識成智,則萬法歸一。故曰「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。」然山河大地,為大家共見,此共業使然。圓智者,不過共中不共而已。且有隨緣,故又曰「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」之語。與拔宅飛升之義不同。再極樂莊嚴,乃彌陀因中發願修成,猶工程師之建設,載在無量壽經,亦與此意有別。
問:「空有相即」,人人易懂,並且經有明文,因其不著空有,空有自然相即,而圓融無礙矣。夫「敵對」者,乃「我執」與「法執」之甚者也。若無二執,法法圓融,何以造成「敵對」?既成「敵對」,何以使其「相即」?(李洛非)
答:「空有相即,人人易懂」。閣下此言,不敢苟同,此理區區即不甚懂,故不便承當。餘問皆是議論,可暫置之。
問:「性修不二」應當是全性起修,全修在性,是為性修不二。若修惡斷,性惡尚在,何謂「性修不二」?(李洛非)
答:「全性起修,全修在性」須知性被惑蓋,惑即是惡,修者修去蓋性之惡耳,惡斷尚有何事。閣下忽云「修惡斷,性惡存」,恐是誤解文義矣。不知「修」是動辭,「性」是佛性,既云蓋性之惡,被修已斷,又云性惡尚存,或將「性修不二」未分體用也。
問:天臺所謂「事、行、理之三毒。事者,虎狼刀劍等也。行者,五住煩惱等也。理者,法界無礙無染即理性之毒也。」不知虎狼刀劍何以為毒?法界無礙無染何以為理性之毒?(李洛非)
問:天臺曰「如來不斷性惡,對惡而得自在。」如來尚有「人相」、「我相」乎。否則能對所對從何而說。眾生所以不自在者,以其有「人相」、「我相」,相對為礙也。吾聞如來達法,於法自在,運無緣慈與無緣悲(如陽光普照)沒有能對之心,所對之境,無往而不自在也?(李洛非)
答:天臺教義,浩如煙海,區區不過毫知釐解,閣下可謂問道於盲,況下問,某經某論,前文後句,俱未言出,不敢斷章取義,不知即言不知,語取實也。
問:惡法在惡譜乎?菩提涅槃在佛經乎?(李洛非)
答:見思十惑,五逆十惡,二十隨煩惱,八萬四千塵勞,皆是惡法,經詳列載,可云是譜。簡單求知,有百法明門論,宜先研討。至云菩提涅槃,有大小涅槃經、菩提經、菩提心經、莊嚴陀羅尼經、離相論、菩提道次第等,多讀自知。且此二事,散見各種經論,為佛法兩大主幹,何得疑經所無。
問:性惡說據說是天臺大師獨有的思想,特異的法門。那麼釋迦如來未證極果乎?否則,天臺祖師何以能有特異法門?(李洛非)
答:性分有惡,是臺家學說,各祖解經各異,此事恆有。道生法師一闡提有無成就之爭,真諦及玄奘師唯識之不同,以及見惑品數,八識九識之異等,不勝枚舉。皆未言釋尊未證極果,天臺言性有惡,乃言其以前,非言其無終。
問:一真法界內,無佛無眾生,佛與眾生都不可說,獨具善惡染淨乎?(李洛非)
答:問義不明,不便率答。
問:公案一、一個和尚問趙州「什麼是祖師西來意」。趙州回答「庭前柏樹子」。二、一個和尚問「萬法歸一,一歸何處」。趙州回答「我在青州時候做了一件布衫重七斤。」三、一個和尚問洞山「誰是佛」。洞山回答「麻三斤」。上述三個公案皆「答非所問」,因為當和尚問「一歸何處」、「誰是佛」時,在趙州或許認為「都是些廢話」、「自性即佛」、「一歸自性」、「自己就是佛還用問」,真是「笨蛋」,於是以「廢話」答問者的「廢話」對否?(王居士)
答:經論顯說,機鋒密示,多少祖師,因機鋒而悟。且此乃生死大事,開場度眾,安能「答非所問」、「以廢話答廢話」。誤會甚矣。再者他們之事,你我皆不在場,插嘴不得,問答不得,未聞靈山拈花,旁人饒舌。奉勸初學,暫將語錄高擱,多研經論,庶少入歧。
問:敢問毛姆說「那些利他主義者,表面上雖是利他,但終歸利於自己,不論是出自有意或無意。」此種論調,乍聽之下實乃謬論,但仔細一想卻不無道理,人云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、「獨樂不如眾樂樂」最後還是自己快樂,這不就是自私了嗎?(王居士)
答:學佛之人,理依聖言量,凡夫之言,皆是無明發聲,素隱行怪,置之而已。若尚辯論,公說公有理,婆說婆有理,各能圓其說。主張利己說者,墨翟博愛,純是利己,即毛氏之論矣。主張利他說者,楊朱為我,純是利他,因各個習私,即是利他,反成為大公矣。
問:敢問學生今後宜走「淨」或走「禪」。學生徘徊不定,請指示。(王居士)
答:貴居士雖未得禪學之正,卻染禪習甚深,不必更張,宜利導之。學佛者,必行解雙修,既不盲人瞎馬,亦不說食數寶。古人有教演華嚴,行尚彌陀者,楊仁山開士是也。有教演法相,行尚彌陀者,梅擷芸大士是也。有教演般若,行尚彌陀者,江味農居士是也。貴居士之氣分,宜法江士,因函中稱常念佛,句句入心,再發願往生,定上品也。學禪須有名師,必多生斷惑,始了生死。學淨但能伏惑,當生成就,難易兩途,不可不擇。
問:師在善果林講經云「心亦沒有的」,繼又說恐大家聽不明白發生誤會,還是希望大家老實念佛不必求解亦可成就,弟子從師學佛在行的方面是本著信願行,老實念佛,在解的方面則亦盡力研究佛理,冀能增強信心,保持正確念佛方法,故對心是沒有的。作了如下的參悟,眾生是由五蘊合成而有身命,而五蘊又分為色心二法,心法是由受想行識合成,既是眾緣和合當屬虛妄,且受想……等本身亦是根塵相對所引起的虛妄相,則心法更是虛妄了,故云沒有,此種領悟然否?(鮮純賢)
答:恐生誤會,還是誤會。心性問題,只許參會,不能講說,經論凡有所云,只是烘雲托月,難道其真。此亦可曰「體絕百非,理超四句。」區區言「心亦沒有的」語氣不如此,意亦難表達,言沒有,乃言沒形質,非言沒事沒理,若言連事理也沒,何故「明心見性」、「見性成佛」、「自性清淨心」、「靈光獨耀」、「性名自有,不待因緣」等等。古德云「智人求心不求佛」,今要換換口味,供養居士,「初學參佛不參心」。
問:師云如真能了知「心是沒有的」則更高了,請問所謂更高,是否就如楞嚴經所云,打破五陰區宇以後就轉識成智,得到明心見性成佛的境界了,抑或只算解悟,不算轉識成智呢?(鮮純賢)
答:區區當日,所言之高,並非真高,乃是二級與初級比,絕非如妙高峰。「轉識成智」更不是今日說的話,待經過無量僧祇,再說不遲。
問:思慧與無分別智的境界有何差別?因思即須研究分辨,無分別智楞嚴經要不起分別心,此二者似有矛盾,弟子迷惑不清。請開示。(鮮純賢)
答:思慧者,思維之慧,此乃對於求學聞道,鑽研其理,由淺而入深,再辨證其所研所知,或正或訛,以客觀為出發點,專求事理之真也。無分別智,乃係破徧計所執,斷除人我法我二執,不起憎愛之平等性智,已得諸法實相之境也。前法可云是因地,後法可云是果地,因求果得,安有矛盾。
問:前往埔心途中,我尚在冥冥之狀態,忽然間,一個念頭掃過腦際。是來的如此的突然,嘩。那真是改變我一生的一剎那,當時我忽然醒悟,為人處事,萬事萬物的道理,就在我心中,是我這點「人性」,它是一切道德的「根」,所有一切世俗上所謂的「善」都是它的註脚,而且人人都有,絲毫不要到外面去找尋,只要你是「人」,生下來就有,而且也就是「人」所以被稱為「人」這個悟是正是邪?(王居士)
答:貴居士喜讀佛典語錄,此乃法塵緣影,忽起現行,是正非邪。所謂悟者,乃知見之了別,尚非見性之悟,不可驟喜。然貴居士夙植深根,今遇法緣,俱屬難得,善自虛心,求師訪友,納入正軌,前途成就,定不尋常。切忌閉門造車,雜亂無次。
問:若天上真有諸「有情」,則不再有食色之慾,此種猜測對否?(王居士)
答:經云,一大千界,有天二十八層,分為三類。從地向上,初有六層,名曰欲界,以其有男女飲食欲也。從而向上之色十八層,空四層,始無此欲矣,此亦大略之言。然諸天亦未斷惑,即曰有情,不離生死,仍稱凡夫。
問:深深感到佛家的境界確實高於耶家與儒家。耶穌說「當行善的時候,右手不要讓左手知道,天上的父,定會賜福給你。」可見最後還有個要求「賜福」得念頭,並非完全出自於無目的真誠。在我認識此佛家一點理論後,覺得儒家的「忠恕之心」、「仁義之心」,耶穌之「博愛」,只是「真如本性」的一點顯現而已。如同一個燈泡放出許多光線中的一束而已。此種觀點對嗎?(王居士)
答:學佛贊佛,理之當然,然贊亦應由所知者贊,若真如法,本難思議,以之與他教較論,每多扞格,不易入扣。至儒家之學,亦浩如煙海,中國文化係焉,古之高僧,無不皆通,且多護念。耶家之書,量雖甚少,吾輩或讀不讀,每未深研,各行各是,不必攀掣,先通本學,再事旁取不遲。
問:在學生的淺見猜測中我認為,不但構成外境物質的四大空,連精神五蘊亦無實性。「心本無生因境有」,既然外境空,心識由外境相感而生,境空,因此心識亦空。又據唯識,知無明乃心識之一種,也應該是空無自性。佛法乃因眾生迷而不覺才有,如無「無明」存在,何來佛法之有乎。既然無明空,可見佛法亦空。由以上推論,「淨」、「心」、「佛法」無一樣可得,全是因緣造化。外境空→心識空→無明空→佛法空。這種連續正確嗎?(王居士)
答:佛家說空,乃佛學之精華,實非儱侗一語了之,雖提出種種之空,絕非一空抹倒一切,若無確切至理,何須嘮叨四十九年。若徒望其文,不究其義,即恐招尤。但此段,似是議論,並非問答,因貴居士好學,謹提幾許葛藤,貢作參考。內中所舉之四空,「心」、「全是因緣造化」。經有之「非因緣、非自然」何解。「境空」又認為「心本不生因境有」。境既空何能生心。「無明空」。既空矣,又何須三祇斷之。「佛法空」。又何言真實義、了義,何勞斷臂求,誓願學,不知求個甚麼、學個甚麼。據在下所知,經訓「空即是色」,教義「一假一切假」,又斷與常是邊見、增減、苦樂、空有,亦復如是。
問:學生猜測「真如本性」,亦是「空」無一物,但是佛性的空非頑空的空,應是空中能生「妙有」的空,這真是奇怪又難以描述的。在我認為,凡是經過吾人思考後所產生的任何一種精神狀況,都已經落入這個相對世界,也就是說,「不可說」、「一說即非」自性,因為當要說的一剎那,就先有「念頭」產生,既有「念頭」,就已經是真如本性的「用」,凡是屬於相對世界的一切概念,都不足以去描述它,一念即非,一說即錯,如果說用人類之概念可以描述它,就如同指「海波」為靜止的「水」,這是錯誤的,只能言「體」、「用」關係。若指「用」為「體」這就不對了,當然無「體」亦無「用」,離「用」不能顯「體」之存在,二者只有相依存在。萬不得已,為了方便解釋學生之旨意,假設「真如」為「電源」,它無聲亦無嗅,即無形亦無相,空無一物,可是若拿「燈泡」接上此「電源」,「燈泡」亮了。「燈泡亮」表示有「電源」的存在,如果說「燈泡亮」就是「電源」本身,這就錯了。真如本性與外界的任何概念亦是如此。比喻對嗎?(王居士)
答:此段有幾句要語,真如本性,「亦是空無一物」。「既有念頭,已經是真如本性的用。」空無一物,是將「空」作無解矣,有即應作「不空」解。合而釋之,即是真如空,念頭不空矣。希參。燈泡之喻,亦不甚妥。
問:當我說「我看到一支筆」。話一說出,剎那間已入概念相對,二元對立世界,而當「視覺」告訴「我」,這是一支「筆」時,此一接觸的一剎那,「我」和「筆」,同時存在,兩者剎那間,心物一體,不可能分開,如果將「筆」拿開,雖然有「我」的存在,亦不能知道有「筆」的存在,換句話說「我」這個概念的生成,是由於有「非我」之物襯托而出。反之如果有「筆」而沒有「我」的存在,根本就等於沒有「筆」一樣,因此當「我」看到「筆」的那一剎那,「我」和「筆」是同時存在,心物合一,主客合一,絲毫分開不得。此合一之觀念對嗎?(王居士)
答:理論不妨說對,心緣於塵境,塵影落印意識,可云合一,但不可執理廢事。設甲看到法官執筆判人死刑,執行死刑時,可謂是甲殺人否。
問:「佛、菩薩為什麼要渡眾生。」我認為如果沒有「眾生」,那來的「佛」、「菩薩」。故佛要渡眾生。反過來說,「佛」、「菩薩」實無「眾生」可渡,因為如果說「有眾生可渡」,則表示有「佛」、有「菩薩」執「我」相,則即非「菩薩」。因此「佛」、「眾生」是「一體」的,若要強加以分別的話,就只能冠之以「覺」、「迷」而已。甚至當一個人說他「覺」了,就表示他還在「迷」之中,那麼要如何才叫「覺」。就只有「不可說」了,因為「一說即非」,一說就入對待?(王居士)
答:如何不可說,金剛經中,說的很明白,是我等一時看不清楚。
問:當我看到「旗子在動」時,乃「外境」感應我的「性體」,而產生「旗子在動」的念頭,這個念頭有如「風」吹水面而起的「波」,因此當慧能看到二僧侶在爭,是「旗動」、是「風動」時,慧能說是「仁者心動」,是否此意。「心」、「物」乃「合一」,因此「心」不在內、不在外,如此解釋對否?(王居士)
答:此意,第六問中已答,可以參考。本問中既云「外境感應我的性體」,是我與旗二而非一。後又云「是否此意,心物乃合一。」前後相違矣。
問:敢問十大劫前阿彌陀佛依何成佛?(王居士)
答:無量壽經,記載甚詳,乃依世自在王佛得證,可查證之。
(二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