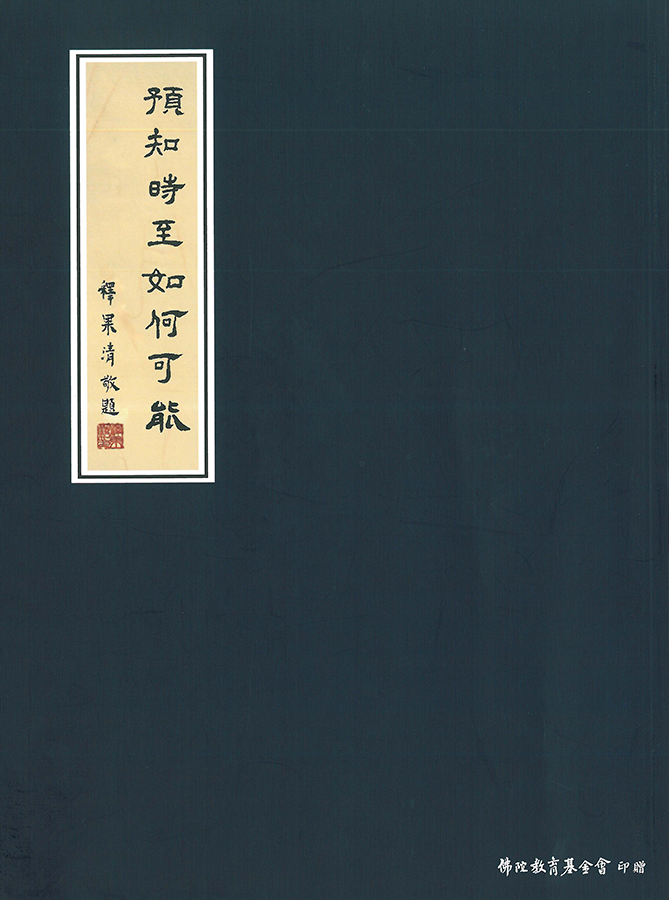 (點擊可放大)
(點擊可放大)
前 言
《預知時至如何可能》,全書共三百餘頁,謹摘錄書中第四節「常慚愧僧『釋印光』」,有關行門方向。從平時的修行,臨終時的應對,及命終的功夫把握,歸納印祖一生的修持成就。於志在往生淨土者,所益匪淺。
一、平時
佛法的本質可以說是教育,而佛法的目標,就是要達到身與心靈的自由,也稱為解脫。然而佛法的精神,也不容忽略現實人生的利益,使生活得以安詳與快樂,這是佛法非常重要的課題。因此如果能使現實生活的品質提升,與滿足未來生活的期許,那麼生命的張力將更具有意義,更為安樂。
所以一個真正能把持正念的人,與平時持名念佛的人,於隨時都能捨報,這兩個方向是相輔相成的。也就是修學不僅著重於未來的期許,趨向菩提大道,而更應使現實的人生更加美滿。因此需要提出印祖在「平時」這一重要的關鍵與依循的方向,將可以探索出印祖的心路思維。
依慚愧為修學方針
首先可以認清的是,現實的生活是以人類為本的,世界上的一切,教育、學術、經濟、科學等各種活動,與人類的關係是最密切的。人面對生命的現實,生命與環境的無常,身與心必定有不可預期的挑戰,也必需要學習與適應。因此面對各種情境,解決痛苦是人性的根本必要,故而人將不斷的運用思維,而思維的目的是為人類解決問題的,所以有必要理出一個合理的方針。
佛法既然是從有情(以人為本)的體認出發,並通達於有情的存在,而有情的存在是物質與精神的因緣而形成。有情為了適應外界各種現象的發生,與內心感受的活動,總必需從有情的存在中去體會與把握。因此,以人類為本的立場下,外界的現象與內心活動達成和諧,才能肯定存在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。
倘若忽略了這個立場,那又將落入另一迷失的觀念。如果落入客觀存在的執著,那易於偏向客觀的實在論。如果直接將外境視為真實的傾向,有可能成了唯物論之缺失。
佛法的立場是依因待緣而成立的,秉持念佛法門的印祖,當不只是為了一期的生命,而持名念佛來保持正念而已,更應該落實在現實生活中的促進與和諧,才能展現出念佛人的張力。我們發現印祖在「平時」這觀點下,其論述的基礎更是身體力行,印祖並以「常慚愧僧」自居,而以「謙卑」的行持做為要點,可知「慚愧」與「謙卑」,是印祖對於淨土宗念佛法門開示,修持的前方便。
慚愧是入聖道的階梯
印祖在復高鶴年居士信中提到,「入聖階梯」是要秉持著「慚愧」二字,印祖說:
居士即俗修真,隨緣進道。執持一句彌陀,當做本命元辰。抱著慚愧二字,以為入聖階梯。
在家居士雖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,也可以依循著佛法的教義修習,當然也是有機會成就菩提大道,這方面必需是通達契理而又能執持的。而在個人不同的時節因緣下,能隨緣隨分循序漸進,這是契機而適應現實的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,要在一呼一吸間,念念不忘、念茲在茲。印祖又強調了,「慚愧」二字,是可以作為進入聖道的階梯。
這是談到一個輔助的下手方法,而且印祖認為是重要的,為何印祖認為慚愧是重要的關鍵呢?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,在考據的資料中,沈去疾《印光大師年譜》中談到,印祖於一八八七年至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潛修,深入經藏,奠定基礎。而筆者於《大正藏》中,慚愧一詞共出現四三三五處,而所觸及的典籍涵蓋了整個經、律、論。印祖自稱為常慚愧僧,可知印祖對於慚愧二字的體悟甚深。因常懷「慚愧」,故對於境界中的人事物,於行持的起心動念之間,是近乎於無我的核心價值,這是得以肯定的。而「抱」之一字有依怙的傾向,也就是在平時的生活,與慚愧合而為一的行持精神。
印祖在回復汪夢松的書信中,更直接指出懷著慚愧的心,如何「萬無一失」,得以往生:
欲念佛求生西方,必須知因識果。身之所行,心之所念,須與佛合。若與佛悖,則縱能念佛,亦難往生。以感應之道,不相交故。若能生大慚愧,大怖畏。改過如去毒瘡,立志如守白玉。則萬無一失,各得往生。
在這一信函中可以發現,印祖開展出如何得以往生捨報的觀念,於平時用功的三個扼要次第,一、由知因識果,二、而能身心與佛合,三、方能感應道交。而要圓滿這修學的真正下手處,印祖更直接指出慚愧二字為輔助,而能萬無一失。
以慚愧水洗滌染心
方針既然已確定,那麼在什麼情境下來行持呢?這是一個歷程的起用與轉化,印祖又如何來安排呢?在復鄧伯誠的開示中,印祖提出「二六時中」持續用功的方式:
佛經教人常行懺悔,以期斷盡無明,圓成佛道。雖位至等覺如彌勒菩薩,尚於二六時中,禮十方諸佛,以期無明淨盡,圓證法身。況其下焉者乎?而博地凡夫通身業力,不生慚愧,不修懺悔。雖一念心性,與佛平等。由煩惱惡業障蔽心源,不能顯現。
印祖的意思是說,通俗的凡夫通身業力,背覺合塵,更應念茲在茲的懺業除罪。即使是等覺菩薩,仍於二六時中禮十方佛,也就是說念念皆不離懺悔,亦即恆以慚人愧己之水,洗滌塵染之心。如此方能「戒淨定明而慧」。換句話說,若不生慚愧,不修懺悔。即使一念心性,與佛平等,然煩惱無明垢染成習,亦難與佛一鼻孔出氣。
當然在現實的生活中,聚焦在一生命體上,即使持續的念佛行持,通俗的凡夫,在這俗緣轉化成法緣的歷程間,不可避免當有起心動念的各種可能。生滅變異的無常,又有幾希能不受因緣果報,而屹立不搖呢?
印祖又如何以「慚愧」二字來面對這樣的情境呢?在回復某居士的開示中可以感受到這一配套的用功次第,印祖說明:
所言異疾,殆宿世之怨業。怨,世每誤作冤。冤,屈也。怨,仇也。怨業病,勿道世醫莫能施功,即神仙亦無從拯救。汝果能生大慚愧,改往修來。以志誠懇切心,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。彼宿世怨業,初則由佛號而即速遠避,繼則仗佛力以脫苦超生,決定不至仍舊纏綿。然若心不至誠,及不生『改往修來,諸惡莫作,眾善奉行』之心。則自己之心,與鬼相鄰,與佛相反。縱稍念佛,亦難感格。乃己心不誠不正,非佛法之不靈不驗也。
印祖認為特殊的疾病,是因為往昔所造的惡業,那就不是世間一般的醫療可療愈的。而印祖更提出更深入的觀點,單一「怨」字即是「仇」的意思,那就肯定了受業報的必然性。那麼在生命無常的現象裏,凡夫又必定讓宿業牽繫,總不免為這幻化的身心起惑受苦。既是承受著眾所因緣而共成,必然五陰(身心和合)常相不調。宿緣來追要逃也難,無常老病,總難以預計啊!
印祖再強調了怨業病的無可醫治,唯有生大愧心,而大慚愧心當必至誠,也需要改往修來。也就是在那一時刻起,那一些宿世怨業,必定會疾速遠避。倘又能念念相續,而必可仰仗佛力脫苦超生,決定不至仍舊纏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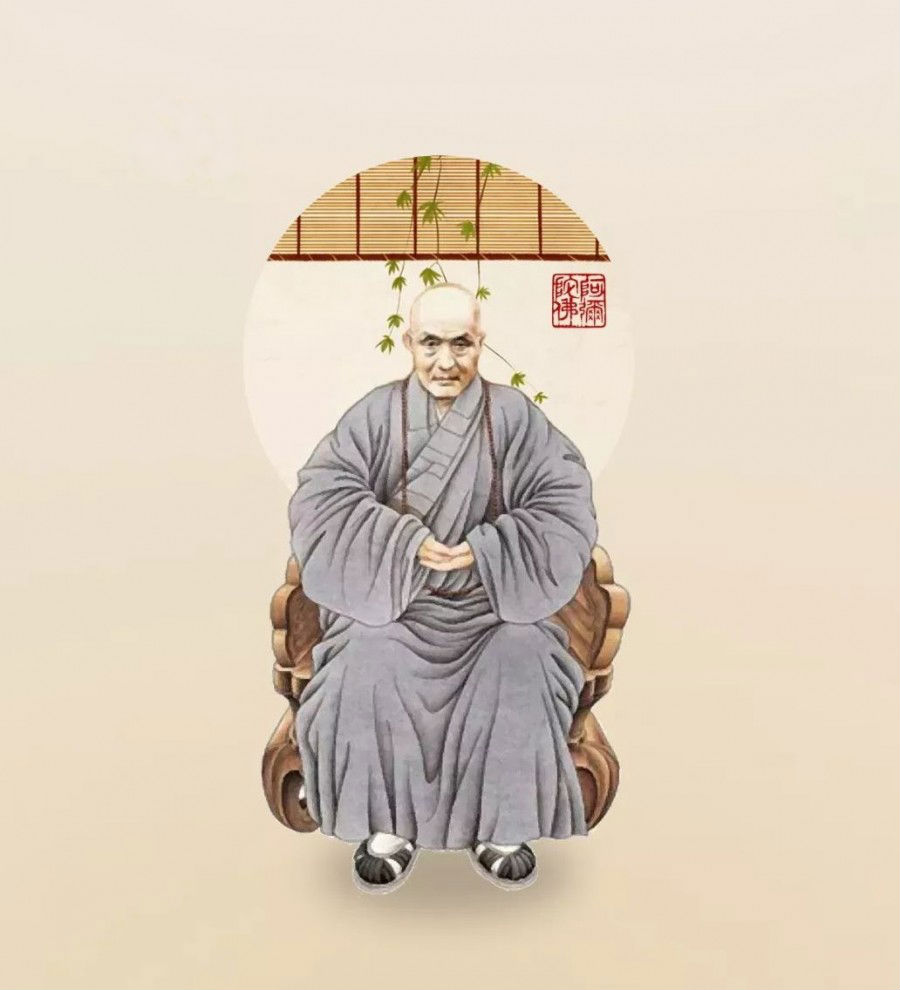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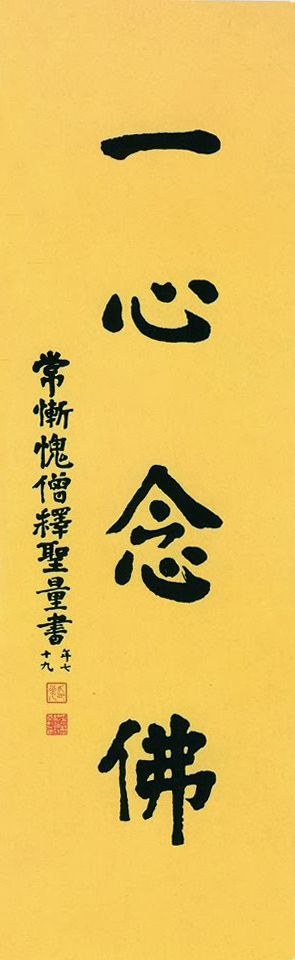
(待續)
【前期連結】求往生有把握.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