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戈與玉帛
●元
亨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
孔子對曰:「俎豆之事,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,未之學也。」
明日遂行。(《論語.衛靈公篇》)
自從周平王東遷雒邑,周天子實際上已經無法號令諸侯,王政不行,禮崩樂壞,於是列國諸侯都在追求武力爭霸。在這樣無序的國際時潮之下,孔子五十六歲時,眼見在魯國不能行道,決定離魯到中原各國週遊,期求明君以行王道。
庶之富之教之
孔子第一站到了衛國,除了因為地理上與魯國相距不遠外,從分封立國開始,衛國一直都和魯國有著的密切關係,甚至其後國家政治的發展情況也很近似。孔子說:「魯、衛之政,兄弟也。」兩國都有著很多的賢者與賢大夫。孔子初訪衛國,《論語》有一章記載:
子適衛,冉有僕。子曰:「庶矣哉!」冉有曰:「既庶矣,又何加焉?」曰:「富之。」曰:「既富矣,又何加焉?」曰:「教之。」
孔子點出衛國治國之大本,要在教化百姓。當時的衛君是靈公,他在位的時間一共有四十二年(公元前五三四年至公元前四九三年)。
其後在孔子週遊各國的十四年裡,曾多次回到衛國,在這段週遊列國期間,比起其他國家,他以客卿身分待在衛國的次數與時間都是最多也最久。
當時在國際上很多人都知道孔子是聖人,孔子對衛國國政的了解也十分透徹,從《論語》中很多篇章的記載,可見孔子與衛國諸多的賢大夫建立深厚交誼,例如蘧伯玉、史魚、衛公子荊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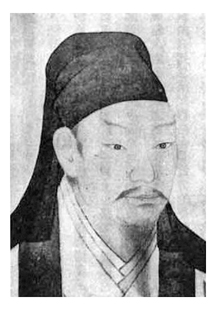
(孔子與衛國諸多賢大夫建立深厚交誼,如與蘧伯玉互有往來。)
無智與無福
依《史記》記載,靈公一開始仍以客卿對待孔子,願意用與魯國相等的俸祿,提供孔子,然而終未重用。《史記孔子世家》說:
孔子遂適衛,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。衛靈公問孔子:「居魯得祿幾何?」對曰:「奉粟六萬。」衛人亦致粟六萬。
靈公因寵愛夫人南子,他在世時就發生了太子蒯聵欲謀殺南子,因而被廢出亡齊國的事件。由此也種下靈公死後,衛君父子爭國的亂因,孔門子路也死於這次災難。
孔子在衛國看清衛靈公只是個見識不高的無道之君,連家都不能齊,勢必會舉國動亂。孔子在衛國來來去去,就在靈公眼底下出現,卻終不獲用。讀史至此,也只能慨嘆靈公的無智與衛國的無福。從《論語.衛靈公篇》的首章即可看出: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:「俎豆之事,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,未之學也。」明日遂行。
靈公所問不是治國大道,卻是戰陣用兵之事,這對有聖人之名的孔子提此問題,真是把治國為政的要旨都弄錯了。可見靈公之問,不論是真心求教或者為測試孔子學問,其動機都是不仁又無道。而孔子回答他,說自己只懂得祭祀禮儀諸事,不曾學過軍事方面的學問,表面上是給了靈公一個婉拒回答的軟釘子,但孔子怎會沒學過軍事?否則他又如何能教得出身通六藝的七十二位大賢?又怎能在齊魯夾谷之會中,預擺軍陣保住魯君並取回國土!
孔子言外之意,正是回答靈公,只要能以禮樂教化治國,從自身做起,並使其家庭、乃至全國都能施行禮治,則國力自強,四方之民自可不征而化,又何需依靠武力去爭霸呢?《論語》「遂行」這兩個字,顯出孔子離開衛國時,不願幫靈公做不仁之事,及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果決心情。
好禮好義好信焉用稼
孔子弘道救世的宏願,總是為世人所誤解,只知以力服人的諸侯又怎能聽進去?孔門弟子樊遲,見孔子所教的禮義不為人們接受,何妨乾脆改學農事以治國吧?《論語.子路篇》有孔子與樊遲的問答:
樊遲請學稼,子曰: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為圃,曰:「吾不如老圃。」樊遲出,子曰:「小人哉,樊須也!上好禮,則民莫敢不敬;上好義,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,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則四方之民,襁負其子而至矣;焉用稼!」
在上位的領導者,若能好禮、好義、好信,則百姓自然能敬、能服、能以誠實之情相待,如此不只本國能教化好,其他四方人民也都會聞風來歸,又何需專講農政呢?可見治國之本,貴在講求禮義及信任。
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,最後卻導致衛國內亂,其所得的諡號為「靈」,在《史記.諡法解》云:
亂而不損曰「靈」。
靈公得此諡號,顯示他在位期間,不能以治損亂,致使衛國陷入太子蒯聵與衛出公的「父子爭國」,牽動多少人的生死。靈公如能用孔子之道,早日實行禮儀,弭平家人蕭牆的嫌隙,化干戈為玉帛,又怎會釀成後來的禍亂?
一國一地,能否蒙受聖人教化,並非有聖人出世,就能嘉惠時人,實賴多方福慧,方得成就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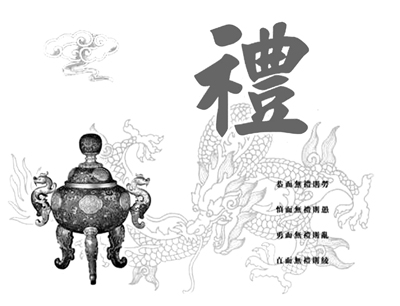
(領導者好禮好義好信,百姓自然能敬能服能以真情相待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