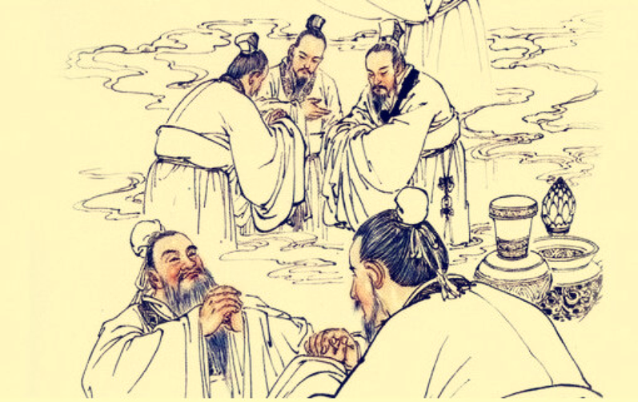這是一篇管仲與晏嬰的合傳。《史記》合傳多是以背景相似或事蹟相關者合併撰述,管、晏為齊國前後任相國,且皆為功臣名相,管仲助齊桓公稱霸諸侯,晏嬰使齊景公顯名於各國,是以合傳。此外,更重要的是在為人上,管仲奢華,晏子簡約;管仲僭越於禮,晏子謹守禮義;兩者間頗有對比作用,亦可見兩人不同風神。
管仲是姬姓、管氏,名夷吾,字仲,諡敬,被稱為管子、管夷吾、管敬仲,潁上(今安徽省潁上縣)人。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法家開啟者,也是創立齊國輝煌國威的政治家。政治上提倡尊王攘夷,對內尊奉周天子,對外平定四方夷狄,因此孔子說:「微管仲,吾其被髮左袵矣。」正是讚揚管仲安定天下的功績。他推行國家新經濟政策,使齊國富強,同時壯大文治武備,使桓公得以九次大會諸侯,一匡天下,成為春秋時代的霸主。
因此,當年公子糾與小白(齊桓公)爭齊國王位時,公子糾失敗而死,管仲寧願被囚而不隨公子糾死,子路認為管仲侍奉公子糾,應忠心不二,且道義上亦不應舍糾而獨活,故稱「不仁」。孔子卻說「如其仁」,為什麼呢?孔子認為管仲雖個人德性有所缺失,但從大局上而言,他安定天下,造福蒼生,這是更大的仁愛。而就管仲言,其心懷雄壯抱負,以輔君治天下為志向,是可以理解的。
然而,千里馬需要伯樂的賞識與推薦,鮑叔牙正是那伯樂。管仲曾舉出五件事,說明鮑叔牙的知遇之恩。一是過去一起做生意,自己利益分得多,鮑叔知道是因自己貧窮而不是貪婪。二是為鮑叔謀劃事情不成功,鮑叔認定是因為時機不利,而不是自己愚笨。三是一再不被國君所用,鮑叔認為是因生不逢時,而非不肖。四是三戰三逃走,鮑叔認為是因家有老母不能死,而非膽怯。五是未隨公子糾死,鮑叔知是因不恥小節,一心想聲名顯揚於後世,而非無恥。故「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鮑子也。」這番話是讚揚鮑叔的知遇之恩,其實何嘗不是為自己的不當有所解釋。
相對而論,鮑叔牙愛惜管仲的才能,珍惜管仲的志向,在為國舉用賢才的前提下,極力推薦管仲。親自迎請,並為他除去刑具,使桓公金臺拜相,而自己心甘情願處於管仲之下四十年。若無鮑叔牙,管仲不過是齊國的階下囚而已,何來功業可言?而齊國也就沒有這番強大基業,鮑叔的功勞,又豈在管仲之下?為國舉才的重要也由此可知。

管仲助齊國成就霸業,卻未能為齊桓公推舉賢相。管仲病重時,桓公問誰可為相?管仲說:「沒有比國君更了解臣子」,未作推薦。《呂氏春秋•貴公》提到桓公問鮑叔牙可乎?管仲說不可。因為鮑叔牙為人清廉潔直,不接受不如自己的人,而且得知他人之過,終身不忘。桓公又問隰朋可乎?管仲也不贊成,惟無人可用下則可以用。但隰朋與管仲同年死,此後桓公更加親近易牙、開方、豎刁三小人,齊國由此衰弱。
《禮記•大學》說:見賢人不能推舉,或推舉而不在自己之前,這就是傲慢。反之,見不賢而不能貶退,或貶退卻不能驅於遠方,使國君無法接近,這更是重大過失。
所以史魚極力勸國君進用賢者蘧伯玉,辭退彌子瑕,但衛君不聽,於是史魚將死時,對其兒子說:「我為人臣,生不能進賢退不肖,死不當治喪正室,殯我於室,足矣。」衛君得知後立即進賢退不肖,此稱為尸諫。相對於此,管仲不如史魚德操的清高,管仲雖逐退易牙等三人,卻未為桓公根絕三子。
《孔子家語》曰:「知賢,智也。」那麼鮑叔的智慧顯然高於管仲。又《孟子•滕文公》說到堯、舜禪讓,以天下為己任,故「分人以財謂之惠,教人以善謂之忠,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,為天下得人難。」此正可用以分析管仲不能舉賢,是因為德性不足的緣故。
再者,管仲財富可比擬王室,有三歸、反坫的行為,但因治理國政佳,百姓富足,所以齊人不因此責備他的奢侈與僭越。所謂三歸,指管仲有三個庫藏。反坫是君主宴客時,飲後放回酒器的高台,依禮管仲也不應設置。
故司馬光〈訓儉示康〉曰:「管仲鏤簋朱紘,山楶藻梲,孔子鄙其器小。」孔子批評管仲器識狹隘,除了奢華、僭越,還因他治理齊國四十餘年,僅能稱霸諸侯,行使霸道,而未能輔佐君王行王道,以及注重財富、軍政,對周朝的禮樂文化造成衝擊。再者,《論語•八佾》孔子說管仲不節儉、不知禮,亦是針對管仲不能正身修德所作的評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