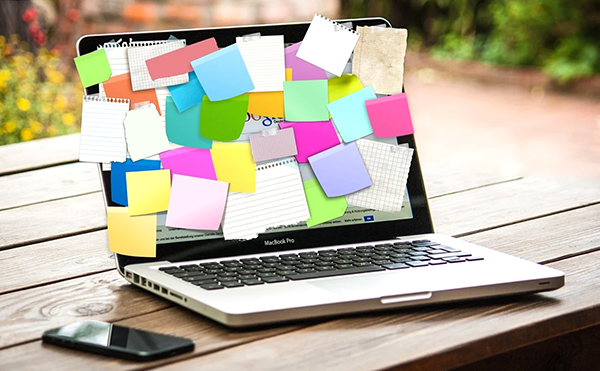
如果修行是不斷放下自我的旅程,扮演「父母」這個角色,正走在這條路上。
從孩子呱呱落地的那天開始,你的生命註定有一大部分要割捨給他。姑且不論別的,只要翻開行事曆,就很容易發現孩子們的大小事,幾乎爬滿了整月的格子,你只能在夾縫中,偷個時間喘息,或趕緊把公事、家務及個人瑣事完成。當然,現代人因工作繁忙,已習慣將許多教養的事務,付費請家庭外的單位(如:托嬰中心、安親班、保姆家)協助處理。即便如此,下了班還是得面對孩子,在工作之外的生活空隙中,你依舊能感受到他的生命與你重疊的那份紮實的重量。
在個人主義及享樂主義高漲的時代,這或許是讓許多人「恐婚」或「恐童」的原因,畢竟,要把自己生命的一大區塊割捨出去,真的得有十分的決心。然而,大部分的人並非做了十足的準備,才擔綱「父母」這個角色的。如果你在這條路上,回首應該會發現,真實的情況是,當你還沒搞清楚狀況時,孩子就已經來到眼前。戲臺的鑼鼓已下,你只能粉墨登場,見招拆招。入戲的,尚且能邊演邊學,把「父母」扮得入木三分;不入戲的,就始終在狀況外,既不能躲,也無法閃,只求快快「卸角」,別被臺下觀眾丟香蕉皮。
如果,大多數人都是當了父母之後,才開始學習當父母的,那麼,從「狀況外」到「入戲」,就是一個修練的歷程。面對一個新生命介入自己的人生,對於自我的框架當然是很大的衝擊。你會發現生活似乎不再優雅、從容、閒適了,因為小至尿布奶瓶,大至成家立業,孩子的人生,似乎有無窮盡的事要操煩。面對生命的框架必須因應孩子的到來而不斷調整,如果自己內在轉化的彈性不夠大,就會發現家庭開始變成「地雷區」,不是因為踩到自己的情緒而引爆,就是踩到對方(配偶或孩子)的界線而衝突。如何不讓家庭變成戰場,不讓自己的「登臺」最後變成一齣鬧/悲劇,遂成為生命的大哉問。
既然生命走到這個當口,死執原本自我的框架已不可行,練習鬆動恐怕是唯一的出路。我們得如實承認,當了父母之後,人生不再像從前一樣輕盈。由於對孩子有責任、期待和愛,肩上的負荷因此沉重了許多。然而,當你願意接納這些大大小小的改變,在面對問題或挑戰時,不再總是用以前的自己來批判現在的自己,心中的那些「喜歡」或「不喜歡」,就比較不容易挑動煩惱和情緒。
比如:現在下班,該回家為孩子做飯了,你會投入在做飯的過程中,而不會上演內心小劇場:「好煩喔!又要煮飯了,我怎麼那麼可憐!要是單身多好!我當初怎麼那麼想不開?」這些內心的喜惡、喃喃自語,來自於過去自己舒適圈的框架,完全無助於解決「現在必須回家煮飯」這件事,只是讓自己越來越煩躁而已。如果,你一直聽這些聲音,最後可能會刺激你對家人發一頓脾氣,結果,溫馨的家人聚餐,變成砲聲隆隆的抱怨大會,孩子覺得你莫名其妙,你也因此認定孩子果然是冤親債主。
又如:明天放假,你突然想到不久前曾經承諾孩子要帶他們出去玩。隔天一早,你會萬緣放下帶他們出門,而不會一直在心裡糾結:「好不容易放假,我好想宅在家裡,哪裡也不想去。當時我是怎麼了?幹嘛隨便答應他們要出門?我真是笨!」發現了嗎?我們的內在常有一個拒絕面對現狀和改變的框架,它牢不可破,只要所遇境不合它意,它就會開始碎念個沒完,最後搞得你情緒爆炸,家人也跟著倒楣。
所以,重點是什麼呢?當你願意把自己設定成「觀察者」或「見證者」,去扮演「父母」這個角色時,你將會發現,每一天和孩子的生活,都是在協助你踏上「放下自我」的修行之路。在每天大大小小、數不清的事件裡,你會願意鬆開自己的執著,讓事件像河水一般流過你的身心,只留下體驗和平靜。即便因為個人好惡而生的內心小劇場,仍會不時上演,但因為你設定自己是「觀察者」,所以你只會看見它,但不會增強它擾動的能量。你會把注意力放在當下,提醒自己鬆開內在,讓事件通過,讓生命帶自己去體驗、去見證,然後成長。
這就是覺知的力量!你覺知自己的角色已跟以往不同,你願意如實接納這個改變,並承接生命投來的變化球。過程中,你會看見自己內在的既有框架在抗拒,甚至發出吶喊,但你只是看見,不會隨之起舞,你會回過頭來專注於當下,提醒自己鬆開執著,讓生命之流穿透自己,帶自己去體驗、見證、學習,然後成為一個不再被框架輕易困住的人。
走到這裡,或許你會突然領悟,為何孔子會說君子「不器(沒有固定型態和功能)」。即便只是在家庭扮演「父母」這個角色,只要帶著覺察和覺知,生命終會將你鍛造成多功能的「變形金剛」。所以,誰說只有在蒲團上靜坐才叫修行呢?當你決定成為父母的那天開始,早已踏上修練之路。

【前期連結】放下無謂的期待,找到親子之間最自在的距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