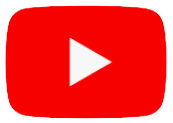古聖經典,蘊含聖人的智慧真理,不能滑眼而過。必得「念終始典于學」,始終常常手不釋卷,如孔子學《易》的韋編三絕,乃有過人的心得。經典唯有「學而時習之」,才能滋長喜悅之情,樂此不疲。
「知之者,不如好之者。好之者,不如樂之者」,這是孔子示人學習的三層次。為好奇求知而涉獵經典,往往淺嘗即止。
清初學者李光地云:「知喜好而不根於心,或他好有以奪之,無躭著不捨,一段精誠。不能久於其道,復而不厭,亦不能溫故知新。」剛開始出自好奇求知,接觸經典,此求知欲望並不是根源於自己內心,信心不足,如再遇其他好奇的事情,這「知之而學」的欲望便被奪去,因為少了一分耽著與不捨的「精誠」。不能安住於一經一典,不願反復讀誦而不厭倦,當然就收不到「溫故知新」的效益。
今人在學校,視課程為學分,學分湊足了,雖未學完全部課程,即欲罷而後已。
明代來知德先生,研究《易經》,自成一家之言。來氏在〈易經來注圖解自序〉說道,因父母生病,在家奉養雙親,沒有出外做官,於是就在家鄉梁平縣(今重慶轄下)的「釜山草堂」讀《易經》。六年下來,一絲一髮的《易》理也未窺得。
於是遠到四川萬縣,客居深山之中,反復研讀《周易》,沉潛到《易》理之中,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。數年後,來知德終於領悟了伏羲、周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位聖人所闡發的《易經》卦象義理,完成了《易經來注圖解》一書,前後歷經了二十九年。
想深造古聖經典之道,靠「知之」而學,難以持久不懈。必須耐得住枯寂,反復沉潛,有一天冷灰豆爆,即有享用不盡的智慧喜悅,這時要他停下來,也欲罷不能。
李光地以「如嗜麴蘖者,雖肴飯可廢。如山水花石癖者,雖傾家財不悔」二例,形容「好之者,樂之者」的境界。像貪杯的癮君子,為了喝酒,不吃菜飯也可以度日。嗜愛徜徉山林、栽花玩石的人,視山林花石如命,即使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。學習若深入「樂之」的境地,不可一日無此君,如有一天無暇風簷展書,便苦不堪言。
經典之所以願反復讀誦,有人是為功名,如蘇秦以錐刺股埋首《太公陰符》,學習揣摩之術。有人是為繼絕學,如西漢伏生,跟李充學《尚書》,用十餘尋(古八尺一尋)的繩子做腰帶,讀一遍繩打一結,十尋的繩子都打成結,《尚書》已誦萬遍,《今文尚書》賴以傳世。但絕大多數人,一遍遍的復誦經典,都是出自「好之,樂之」。如漢儒賈逵,喜好《春秋左傳》,每日課誦一遍。東晉的殷仲堪,三日不讀《道德經》,便覺舌根僵硬。
孔子好古敏以求之,誦詩讀書,有如「與古人居」,尚友古人。如孔子讀《周易》,「韋編三絕,鐵擿三折,漆書三滅」,穿簡冊的牛皮繩斷了好幾回,穿引用的鐵針被折斷好幾次,寫經的漆被磨滅數回。一部《周易》,孔子平居閑暇則「玩其象而觀其辭」,有事猶疑不定則「觀其變而玩其占」,番番的讀,遍遍的誦,探賾索隱,鉤深致遠,最終能完成「十翼」的研《易》心得。
好之樂之,必肇因於「信而好古」,唯有深信不讀經典是人生莫大的損失,乃能誓不放棄。
孟浩然詩云:「一日不讀書,心荒如廢井」,廢井則枯竭無水。人活著若無源頭活水,終日沉浸在膚淺的網路手機,心智不能開發,視野限縮於日用生活,憂患無從排解,何其苦哉!若好樂學習經典,則與千百年前的聖哲,把手言歡,汲取前言往行,澆熄今生的憂悲苦惱,可獲得如陶淵明「每有會意,欣然忘食」的忘食忘憂。

(王維畫《伏生授經圖》,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)
【前期連結】熟誦《論語.述而篇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