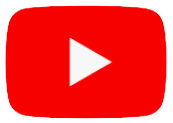器者堪用的器具,一器要精良,全看沉潛功夫。朱銘,原是民間雕神桌工匠,年長後不甘平庸於世俗,用心將雕塑藝術化,然後鼓起勇氣,將作品呈給雕塑大師楊英風。經大師指點,朱銘一心遵循教誨,歷經八年的學習提拔,青出於藍,楊英風甚為欣慰。師不必賢於弟子,弟子不必不如師,故能成器。
游藝而成器
子貢在孔門受教多年,想評量自己的學習進程,一日他問夫子:「賜也何如?」孔子說:「女器也。」子貢知夫子要弟子學「君子不器」,若只成一器豈非還未入門?所以他立刻加問:「何器也?」孔子說:「瑚璉也。」是宗廟大器啊!
「賜也達,由也果,求也藝,於從政乎何有?」這三位弟子自入孔門皆能沉潛悠游於六藝,故能成器。子貢人情練達,子路辦事果決,冉有多才多藝,於從政何有困難?
依仁而不器
器大者成大事,器小者致遠恐泥。孔子教學,首要門人學習六藝,成有用之器。繼而勸人不可畫地自限,不以成器為滿足,還須提升到「君子不器」。君子以群體利益為念,一人一個病,一人一個需求,若不熟悉百工技藝,如何能「安人」?一事不知,儒者所恥,心中有仁為根者,視人如親,想厚以待之,必不會得少為足,自然願廣學多能以安眾,漸漸塑造出「不器」的大才。
試看孔子何以「多能鄙事」?他十五歲立志學習修己安人之仁學,禮樂射御書數非精不可,一者可安邦定國,再者可設教傳學。若眼光短淺,僅圖個人名利,即使精通六藝,也只是多具才器的能人,少了「仁」的根本,所學才器無法安人心。北宋亡於宋徽宗,《宋史》說他沒有「晉惠之愚」,也不像「孫皓之暴」,卻「恃其私智小慧」,雖精通書畫,擅長樂律,因用心偏於一邊,排斥正直之士,愛用章惇、蔡京、童貫等「姦諛」小人。故《宋史》評論說:「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,縱欲而敗度,鮮不亡者,徽宗甚焉,故特著以為戒。」徽宗熱中於多才多藝,於國政懈怠放逸,最後亡國辱身。孟子說:「立乎人之本朝,而道不行,恥也。」具才器而無高遠的理想,不可任高位。因位居大位,手握權柄,應有燮理陰陽,調和鼎鼐的本事,這非大器者難以承擔。
志道為法器
孔子見顏淵「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」,日子太清苦了,勸他何妨從政。有恩師大力推薦,享國俸祿,一般人何樂而不為?顏淵寧願「安其學而親其師,樂其友而信其道」,以學夫子之道為樂。曾子,穿破舊衣服耕田,魯君要送他一塊封邑,說:「請以此修衣」,用這塊封邑的收入作些新衣服。曾子不受,魯君反覆派人來,曾子一再拒絕。曾子擔心「受人之物畏人」,拿人的手軟。孔子得悉後,說:「參之言,足以全其節也」,曾參所言,可以保全氣節。
顏、曾二人,如何能視富貴如浮雲?這兩位是孔門「德行科」數一數二的大哲,自入孔門,即立志于心性之道,心心念念志于道,時時據于德,在道業德行中,仰之鑽之,獲得無盡喜樂。世間的榮華富貴,如浮雲幻影,怎能與心性之樂校量?顏、曾二人,精游六藝堪成大器,懷抱仁心,更提升為不器之資。因心志於道德智慧,深心體念孔子弘道的志業,故一心學道,立道而成道,最終能如孔子為天之木鐸,志願作個「凡有血氣者,莫不尊親」的法器。
嗣闕里遺音
儒以「尊彝」為宗廟貴重的法器,喻以道治國利天下之才。孔子困於陳、蔡,顏淵云:「夫子之道至大,天下莫能容。雖然,夫子推而行之。」孔子笑說:「回﹗使爾多財,吾為爾宰。」能得孔子為宰輔,那顏淵豈非南面之才!惜乎,顏淵,不幸短命死矣。
曾子則老壽九十,一生修學有成,以弘毅的法器自期,終身講學,嗣闕里之遺音。齊、魯之間,學者多出其門,故後學獨稱「曾子」。《論語》一經,除孔子之外,稱子而不稱字者,唯有曾子,堪稱傳法之器。

【前期連結】論語的「能近取譬」.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