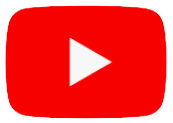熟靠志切散課
世俗人有世俗事,如何練到動念即是「這個」佛號?雪公云:「倘能志切解脫,知善方便,百亂不能移其志,萬事不能忘洪名。白樂天云『饒教忙似箭,不離阿彌陀』,如此謂之熟。全在薰習工夫,打成一片。苦樂忙閑,皆是這個,生死也是這個,故能往生。」有真切的厭離生死心,有真切的欣求極樂願力,則善知各種方便,再亂也不忘「這個」,再忙也不忘洪名。即使是生死交關之際,心頭也有佛號,為了往生。
然百亂不移志,萬事不忘佛,乃上根利器,聞道便勤而行之。中下根人,忙亂遇事即忘這個,如何能熟?應自訂「散課」,以約束心志。雪公在《佛學問答》說:「念佛分定課散課,定課或朝暮二時,或再加入任何一時。作此課時,以坐為佳,必求心定不亂,課畢即回向之。散課則於定課以外,只要有閒暇,不論行住坐臥,皆可行持。」有人不習慣作散課,說──現在事情多,待將事少再定心來念。雪公也加重口氣說:「凡夫家居,安能無事?若待事少再念,則永無能念之時矣。要在自己觀機利用時間,作事用身用手,念佛用心用口。定課但能早起半點鐘,即能照作,散課隨時隨地,皆可執行,不管心亂不亂,總是一直念去好。」願此一報身,得生極樂,若不肯將一句佛號念得熟,云何有信有願?信不真,願不切,命終沒個人依怙。
明末,山西萬固寺附近有一座讚歎寺,寺裡有老僧義秀法師,日課佛號十萬聲。有貧寒士子來依附。多日後,義秀觀察此士子,行為不檢,斥責他:「汝真賊也。」士子懷恨,邀來徒黨,乘夜襲擊義秀。最初一擊,義秀念佛洪亮。再擊時,義秀念佛聲雖微弱,仍持續不斷。臨死,佛聲不絕,還將被打傷的腿盤坐而逝。紫柏大師歎服說:「非五十年志氣堅強勁正,烏能至此?」義秀精進被殺,因是多劫夙殃,卻因熟念佛號,顛沛必於是,縱死亦生淨土。
張一留居士是印光大師弟子,他回憶道:「我告訴師父,自己整天被俗務所困,在瞻園忙得很,心定不下來。」印祖說:「隨地隨時,皆可念佛,瞻園與祇園(佛陀講經的精舍)沒有兩樣。」念佛不必選擇時地,無一時無一處不可念。就像我們的第七識,無時無刻不執著有個「我」,把「我」換成佛號,誰能打斷?
有定課何須熟
有人疑惑:「念佛,有早晚定課,足矣。何須費心練習熟到『動念即是這個』?」雪公答道:「以二課為念佛時,課畢則非念佛時,如此一曝十寒,功夫何能成熟?作課時固然念佛,不作課時,仍有影響。儒家謂『道也者,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』,儒家修齊治平,皆是道也。佛家搬水運柴,掃地焚香,撞鐘擂鼓,吃飯睡眠,皆是念佛。第七識不斷我想,何嘗作一切事,能打斷『我』!若把我換成佛,不會一作事便打斷佛。」發心念佛,即是有道之人,道豈可「須臾離也」?心有一會兒不在道,即是無道之人。心中無道便是「失念」,心無佛號正念時,即爬滿煩惱。煩惱即惑,有惑則造業,造業便逃不過苦果現行。
淨土法門,貴在具足「信願行」三資糧,蕅祖在《彌陀要解》云:「非信不足啟願,非願不足導行,非持名妙行,不足滿所願,而證所信。」對彌陀、極樂淨土,真信其有,乃肯發願往生。有往生切願,乃肯執持名號。唯有持名念佛,乃能圓滿往生大願,證明所信的彌陀、淨土都是真實的。所以淨土行人,當在持名妙行著力,能念到「一心不亂」最佳,不然就要以佛號「伏惑」,最不濟也要勉力念到熟。雪公云:「若問補救辦法,還是多念。東長西短,是是非非,但得放下,即時放下。縱再不得一心,也要念到一個『熟』字。習慣自然,臨終助念,心願往生,即得往生。」
功夫熟有功效
淨土法門,在八宗中最簡易可行,理應萬修萬人去。然而事實上,卻是雖行而未必有果者多。雪公來臺三十年,每年送出上百張的陀羅尼經被,親見三千多人往生。雪公在〈心口若相應 立見佛菩薩〉的佛七開示說:「在三十年內,第一個十年往生的有好幾個,往生的現象很不錯。第二個十年就少了。到現在第三個十年,就寥寥不過幾位而已。功夫已經不行了。」念佛必得求當生往生,不往生是沒結果,所以學淨土法門要有把握往生,若不能成就,便是「苗而不秀,秀而不實」,這要幹什麼?雪公說:「不論顯密,功效無二理。功夫成熟,則行法有效。功夫不熟,則行法無效。效與不效,在乎行法之人,而不在法。」
念佛功夫練得熟,現世吉祥,消災免難,他日功滿,蒙佛接引到蓮池,皆得大效驗。一句佛號,活著時念不熟,命終從識田跳出的,不是佛號,而是熟悉的人我是非種子,面臨的下場是什麼?經云:「單己無侶,入大黑暗,處大艱險,沒溺生死,長流大海。」又回到苦海無邊的六道輪轉,無人救護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的苦,細思深恐。唯有趁著還有一口氣時,熟念彌陀吧!
(全文完)

【前期連結】只要功夫熟 何愁路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