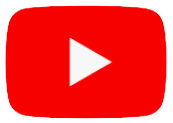宋代惠懃禪師,舒州(今安徽省安慶市)人,宋徽宗賜號佛鑒。善悟禪師,洋州(今陝西洋縣)人,自號高菴。拙菴德光禪師,曾談到兩位高僧的一段行誼。
另備食物獨啖
佛鑒禪師住持舒州太平寺的時候,高菴禪師擔任維那(注一)。當時高菴年紀輕,志氣豪壯,很少有人能令他滿意。有一天,到齋堂用餐,正值打板的時候,他看見住持的侍者用另外的器皿裝著飯菜,放在佛鑒面前,高菴便大聲說道:「身為五百僧眾的住持和尚,這般挑食取捨,怎麼能夠作後學的楷模呢?」高菴一時忍耐不住而說出這些話來,他只從道理論是非,而沒有見到事情的全貌。這就是所謂的有得有失。
佛鑒的胸襟,如山高海闊,好像沒有聽見一樣。高菴看見佛鑒臉色沒變,因而生起疑心去詢問侍者,才知道擺在住持和尚面前的,原來是水虀菜(清水煮白菜)。佛鑒禪師向來有脾胃的毛病,不喜歡吃油膩,所以另外置放水煮清淡的水虀菜。
以理通諸障礙
高菴因為自己說錯話,感到慚愧,便向方丈請辭維那職務。佛鑒用愛語調化他說:「維那所說的話,很合乎道理。由於我惠懃有宿疾,所以才這樣做。曾經聽聖人說:『以理通諸障礙』,以道理貫通各種障礙。現在維那以合乎道理的話,使大眾知曉我所吃的食物,不優於僧眾,這有何妨礙。大眾中有所疑惑的人,都不會再懷疑了。維那的志向與骨氣,高明寬廣遠大。將來必定成為禪門的梁柱,有如磐石一般的安穩。今後相處,希望不要因為今天所說的話,耿在心頭而產生隔閡。」
後來佛鑒禪師遷居主持智海寺,高菴禪師去了龍門寺,成為佛眼禪師的嗣法弟子。
主賓皆有道者
《禪林寶訓筆說》評論說:「此篇見古人智量深妙,主賓皆有道也。」雪堂禪師曾說:「惟有德者,以寬服人。」惟獨有德行的人,以寬宏度量自能服人。高菴禪師氣魄雄邁,若非佛鑒襌師有海闊天空的度量,賓主必定會有間隙。
蓮池大師說:「以嚴正攝心,則心地端;以嚴正執法,則法門立。」高菴禪師的操履實踐,可為典範。佛鑒禪師曾說,佛眼禪師的弟子中,唯有高菴勁健挺直,不徇私情;為人沒有什麼嗜好,作事不援引朋黨;清淨嚴正,端恭謹慎;始終以名節自立,有古人的風範。近世僧人,很少有人能與他相比。
恩惠德行兼具
法眼禪師說,主持寺院的根本,在恩惠與德行,二者須同時並行,缺一不可。只有恩惠與人,而自己不修德,則不會得到人們的尊敬。自己有德,而不惠及眾人,則人們不會歸心依附。
以高菴禪師的行誼為例,他住持雲居寺時,聽到僧人生病移居延壽堂(注二),就再三嘆息,好像自己的孩子生病一般。他早晚都去問候生病的僧人,甚至於親自煎藥煮食,親口嘗過冷熱後才給病僧服用。如果遇到天氣稍微寒冷,他便輕撫病僧的背,問說:「衣服穿得夠暖嗎?」天氣炎熱,就觀察臉色,問說:「是不是太熱了?」如果不幸去世,都按照禪林禮制規定,由寺院出資安葬。由於禪師的美好德行,獲得眾人的尊敬,及雲居寺僧眾的信從與感念。蓮池大師在《緇門崇行錄》中對此讚歎說:「經稱八種福田,看病第一,豈不以衲子無家,孤單湖海,伶仃疾苦,真可悲憐!作僧坊主,而病不於我調,死不於我殯,豈慈悲之道乎?凡住持者,宜以高菴為法。」
根據《僧寶正續傳》記載,佛鑒禪師於宋徽宗政和七年十月八日,沐浴更衣,端居丈室,手寫別故舊書數幅,停筆而化。高菴禪師於宋高宗紹興二年七月一日,趺坐而逝。

【前期連結】上授下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