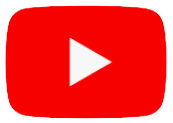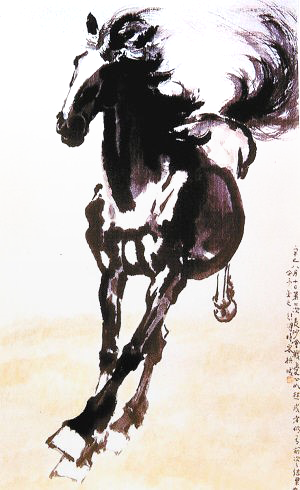
信得決願得切
未經歷的真實境界,不能解,又無法證實,要如何接受?唯有信而已。真實的道理、確實的德行、務實的能力,雖肉眼不見,充耳不聞,凡意不測,但它出自佛語、佛願、佛讚,教人如何不相信?
如念佛往生淨土,有釋迦金口所說,彌陀所發四八願力,諸佛轉讚勸生,諸佛如此諄諄相告,「此而不信,真不可救。」佛語都信不過,世間還有誰的話可信?若深信不疑,即能激發「雖千萬人,吾往矣」的實踐動力。
修淨土法門,深信之後,並不是著手研解,而是「發願」。願者志求滿足,心心念念不忘往生淨土。行住坐臥,起心動念,吃喝拉撒,順境逆境都不忘「這箇」。立住這番志向,則時時自制其心,放逸時,立馬一鞭,迅速回歸正道。稍有懈怠,彷彿被人大呵一聲,精神即刻抖擻,旋即拉回正念。
信得決,如掌管前導者,立定腳跟,不偏不倚。願得切,如在後鞭策者,不容你停頓歇息。有前導,有後鞭,則生西目標永遠懸在前頭,在世一切都為這箇而活。有信有願自然有行,縱或念佛散亂不得一心,蕅祖說:「亦必往生。」
不生一念疑心
信得決者,遇順逆境界決不退轉,再逢他法也決不改修,老實念佛,決不求奇異境界,惟待淨業成熟而已。永嘉某居士想修淨土,卻怕無有效驗,四處詢問誰念佛有效驗。印祖得知後,呵斥說:「修行淨土,有決定不疑之理。何必要問他人之效驗?縱舉世之人,皆無效驗,亦不生一念疑心。」何以故?印祖說,修淨有效,出自佛祖誠言。若要問他人念佛有何效驗,那是「信人不信佛」,中心無主,信不決之輩。
古德云:「士大夫英敏過人者,多自僧中來。」如東坡前世是師戒禪師,今生猶保有超俗的佛法知見,無奈「五濁惡世多諸退緣」,雖知西方有彌陀,但信心不堅決,以至今世迷而不返,錯過此一人間報身,繼續去投胎輪迴,良可歎也。
蘇軾夾禪夾淨
蘇軾,被貶海南儋耳,行李箱裡攜一軸阿彌陀佛像,人問所以,他說:「此吾往西方公據也。」雖然隨身攜帶阿彌陀佛像,但蘇軾平日醉心於山水享樂,如徹夜遊赤壁,「洗盞更酌,肴核既盡,杯盤狼藉,相與枕藉乎舟中,不知東方之既白」,如此生活,恐無念佛定課。
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,蘇軾逝於毘陵(今江蘇武進),臨終有道友惟琳禪師在他耳邊,大聲說:「端明勿忘西方!」他卻說:「西方不無,但箇裏著力不得。」另有一道友錢濟明也隨侍在側,提醒他:「公平生學佛,此日如何?」他說:「此語亦不受。」蘇軾學佛,夾禪夾淨,腳踏兩船,信不決,豈有往生之分!
厭娑婆欣極樂
修淨土有切願者,必「一切時中,厭惡娑婆生死之苦,欣慕淨土菩提之樂」,念念想出離五濁惡世,心心盼望早歸極樂故鄉。
瑩珂法師,讀了《往生傳》後,斷食三日,一心念佛,蒙佛入夢安慰說:「汝尚有壽十年,且當自勉。」常人若得此延壽佳音,誰不慶幸?瑩珂法師出人意表,說:「設有百年,閻浮濁惡,易失正念。所願早升安養,承事眾聖。」寧可早日上升安養,不願待在娑婆一天。厭至極處,欣至極處,此等志願深契彌陀悲願,三天後佛即來迎。
求生西無攀緣
一生殺牛的張善和,妻子平日親近三寶,有僧人屢勸他改業,置若罔聞。臨終,見所殺牛來索命說:「汝殺我。」張善和驚恐萬分,忙叫妻子請僧人來救。僧人為說《觀經》第十六觀下品下生觀,教他「具足十念,於念念中,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。稱念佛名,即得往生極樂世界。」張善和左手擎火,右手捻香,轉身向西,厲聲念佛。念不到十聲,他說:「佛來也,已與我寶座。」
張善和一生造殺業,何以臨終幾念即可往生?戒顯法師在《現果隨錄》云:「死臨冥界,獄火在目,大怖切心,更無攀緣,更無審顧。」願得切也。他見被殺的牛隻來討命,地獄相現,既驚且懼,此刻於娑婆毫無耽戀,且得知至心念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,便奮不顧身的死命念佛,果然「求生之意,彌加敦督」,至心一念,立感彌陀相應。有願即有力,願力能勝業力,張善和有切願鞭策,盡此一生入淨土,羨煞多少悠悠忽忽念佛人。
功課決定不缺
信不真,願不猛,雖念到風吹不入,雨打不溼,如鐵牆銅壁,也沒往生的資格。觀諸多往生實例,真能得一心者寥寥無幾,他們為何能生淨土?信得決,願得切,自從發心修淨土後,日日有念佛功課,決定不缺。
身有病痛,不廢功課。家有紛爭,但念彌陀。逢災遇厄,唯佛是賴。不跑道場,安坐家中,終日以念佛為要務。天天有信有願,匯集成豐厚的往生資糧,最後總把一切送日西,水到渠成,淨業成矣。

【往期連結】不可視為兒童之業──弘一大師的讀誦經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