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一章書,漢宋明清諸儒注疏無多,有亦過於簡略,其中「女子小人」究何所指,並未切實舉出,以致世俗多謂概括而言,造成困惑。此不辨明,以下三句注疏,便無著筆之處,自然受彼俗解淆亂。
《論語˙陽貨篇》,子曰: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,遠之則怨。」這一章經文,漢、宋、明、清儒家學者的注解不多,如有也過於簡略,經文中「女子、小人」所指的究竟是什麼,也沒有切實的舉出來,以至於世俗大多認為是概括的說,造成困惑。女子、小人的涵義不分辨清楚,以下三句經文的注解,就沒有下筆的地方,自然會受到這世俗解釋的混淆。
茲先說明概括之謬。以女子言,有女中堯、舜,巾幗英雄,賢母良妻,孝女烈婦等,各經傳中,所載甚繁,實未概括擯斥。至於小人,則有小人儒,匹夫匹婦之諒,硜硜守信之小人,學農圃之小人樊須等,亦非盡是不肖,何以下文皆加貶辭?俗解文理,既與事實逕庭,顯係未達,亦歸無詳注之失,極應研討,破除從來困惑。
現在先說明概括解釋的錯誤。以女子來說,有女中堯、舜,巾幗英雄,賢母良妻,孝女烈婦等,在聖賢撰述的各種經傳中,記載甚多,事實上對女子並沒有概括性的予以排斥。至於小人,則有學為正心修身的小人儒;堅守信用的普通男女──匹夫匹婦;像石頭一樣堅硬,守信不移,不能變通,只可辦小事的硜硜小人;學習種穀種菜的小人樊須等等。他們並不全部都是不賢的人,為什麼下文都加上貶損的語辭?世俗理解的文辭義理,既然與事實有很大的差距,顯然是因為未能通達文義,也是由於沒有詳盡的注解作為依據所導致。因此應該盡力研究討論,以破除從過去持續到現在的困惑。
本刊一三一號載王教授〈論語有為而言例〉一文,根據經史,闢此俗解虛構,可取參考,匡正之功非尠。
本刊一三一號所載王教授〈論語有為而言例〉一文,根據經史,駁斥這種憑空構想的世俗解釋,可以採取,作為參考,對錯誤的改正,功勞不小。
惟朱注言,小人謂僮僕,女子謂臣妾。劉氏《正義》謂:「此為有家國者,戒也。」又引「開國承家,小人勿用。」之言,較朱有據。然未言及女子,仍欠周密,但亦由寬反約,均有範疇而已。
但是朱熹的《論語集注》,說小人是指僮僕(僕人),女子是指臣妾(服賤役的男女)。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說:「此為有家國者,戒也。」這是為了給當家的人勸誡;又引用《易經·師卦》爻辭:「開國承家,小人勿用。」建國受封為諸侯,立家受封為大夫,不可任用沒有學問道德的小人。這個講法比朱熹的注解有根據,但是沒有提到女子,仍然不夠周密,不過也從寬廣的概括解釋回歸簡要,都有了範圍。
(待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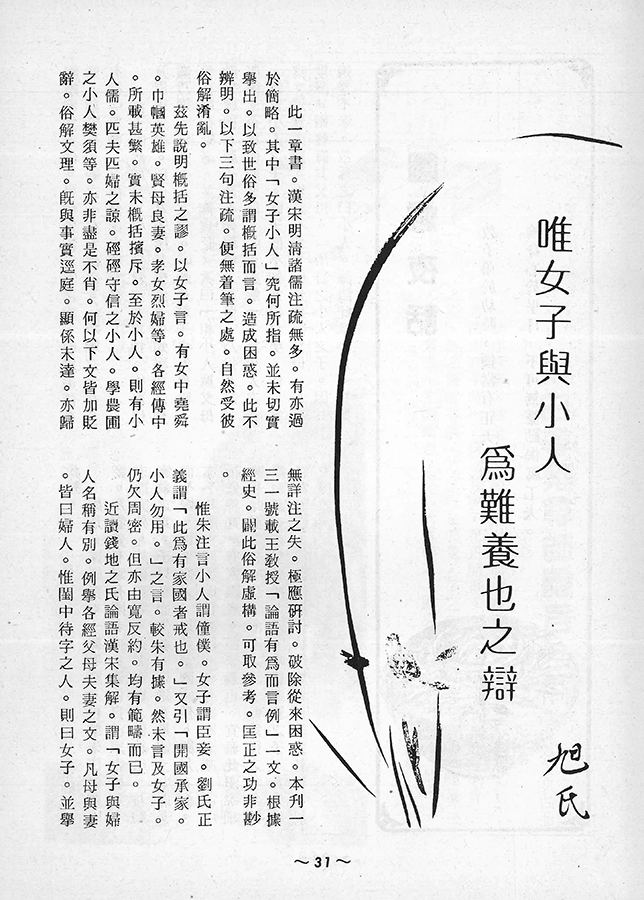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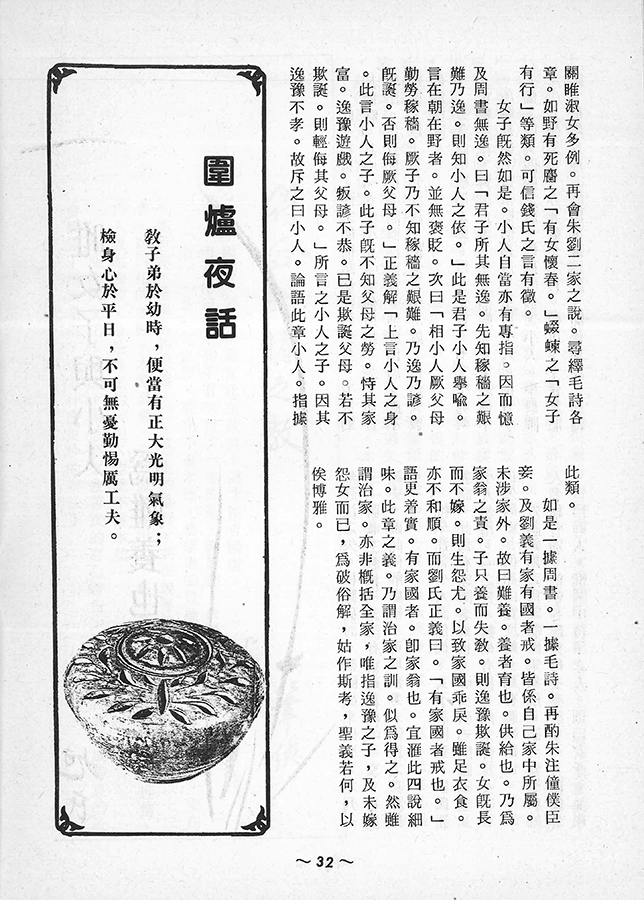
【前期連結】沃枝葉不如學根本